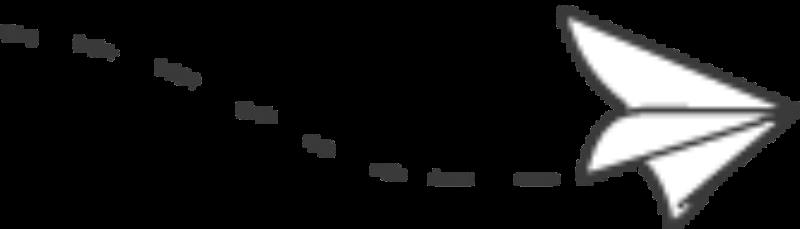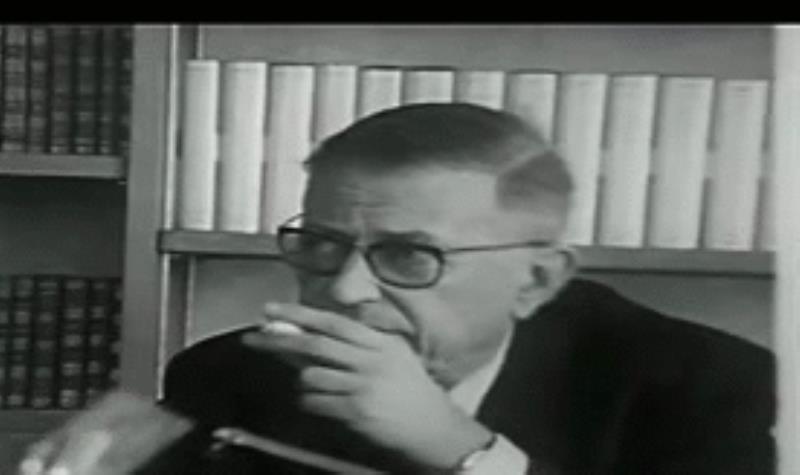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xué)家之一。1964年
,薩特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但是他主動回絕該獎項,成為第一位拒絕領(lǐng)獎的諾貝爾獎得主。薩特強調(diào)人對歷史的影響作用、人的主體性、人的自由選擇性
。他的存在先于本質(zhì)、自由選擇學(xué)說等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1980年4月15日晚上9點左右
,也就是四十年前的今天,薩特病逝于巴黎。而這一刻,薩特將死亡的可能性變成了必然。死亡是一個中國人有些忌諱的話題
,這也許是因為這個話題太重要曾經(jīng)
在英國作家安德魯·利克寫的薩特的傳記《薩特》中
死亡是什么?
海德格爾曾提出死亡是我們“自身最大的可能性”
它并非一首協(xié)奏曲的最后那個決定了之前一切的音符,而更像是正在那個鋼琴家頭頂坍塌的屋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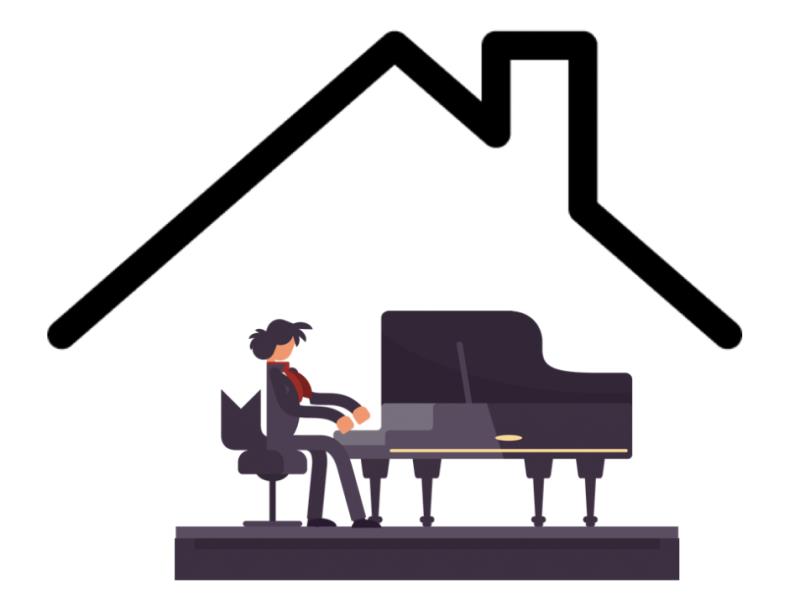
沒有“準時”的死亡
而他對死亡產(chǎn)生的這些一看法,與戰(zhàn)爭密不可分
1929年11月,薩特開始服役
而內(nèi)在遭外在的終極入侵就是死亡本身:“[死亡是]在我自身最內(nèi)心深處的外在的出場?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奔词顾劳霾皇且环N很大的可能性——由于薩特不是一個前線的戰(zhàn)士——它至少是一種可能性 應(yīng)該如何看待生死 薩特在晚年與波伏娃的對話中曾經(jīng)表示 他認為它是很自然的:“死亡說到底是向自然的回歸并肯定我是自然的一部分 薩特認為,寫作不斷推遲死亡的過早到來 從九歲開始——如果我們相信《詞語》(薩特自傳小說)中所言——薩特確信他已經(jīng)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如前面所說 薩特通過寫作 就像一個現(xiàn)代的山魯佐德(《一千零一夜》中宰相的女兒 正是據(jù)此 當他寫作時 例如在1940年3月27日 -End- 編輯:黃泓 觀點資料來源: 《烏托邦的故事:半部人類史》 emily_wangwei(王薇) 在緊缺的醫(yī)療資源面前 拋開那些似是而非的直譯吧,古人的棺材板要壓不住了 大師身邊宜聆教 未名湖畔好讀書 點擊「在看」找尋屬于你的烏托邦 本文地址:http://www.mcys1996.com/lishitanjiu/148796.html.
聲明: 我們致力于保護作者版權(quán)
上一篇:
閻錫山批判蔣介石武力統(tǒng)一兩人關(guān)系惡化
下一篇:
戲劇大師布萊希特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