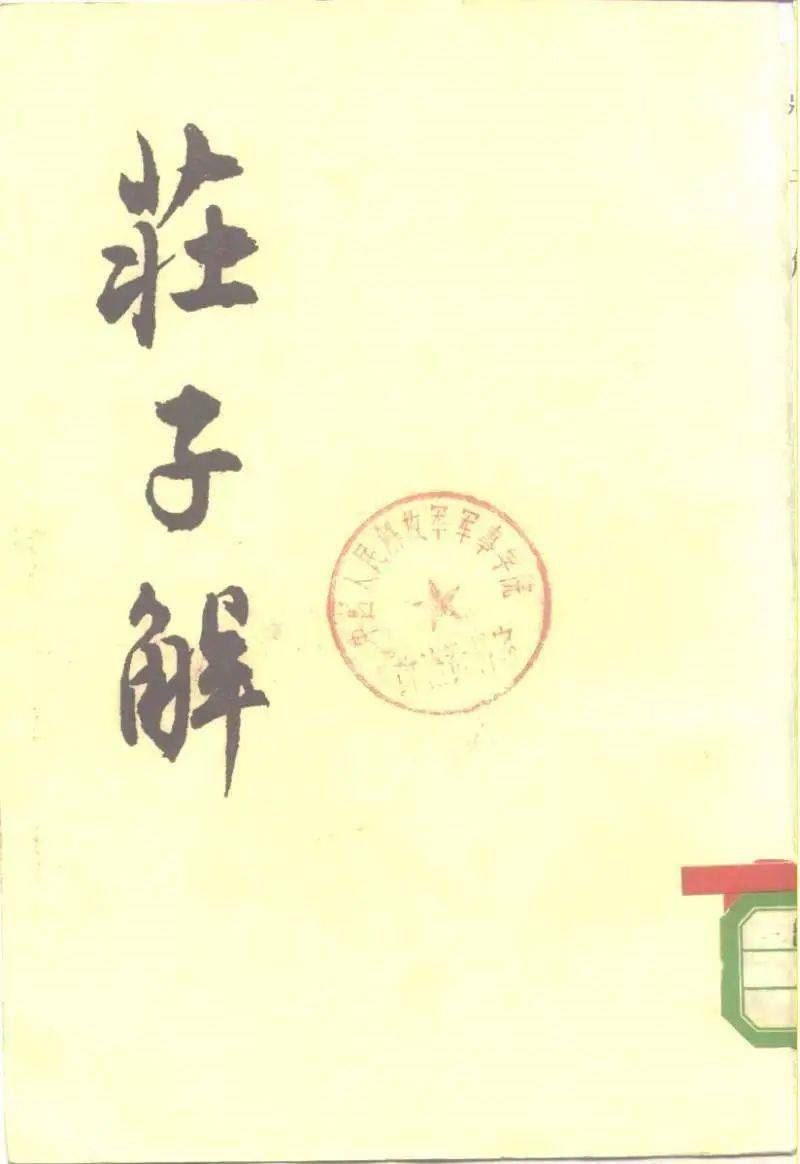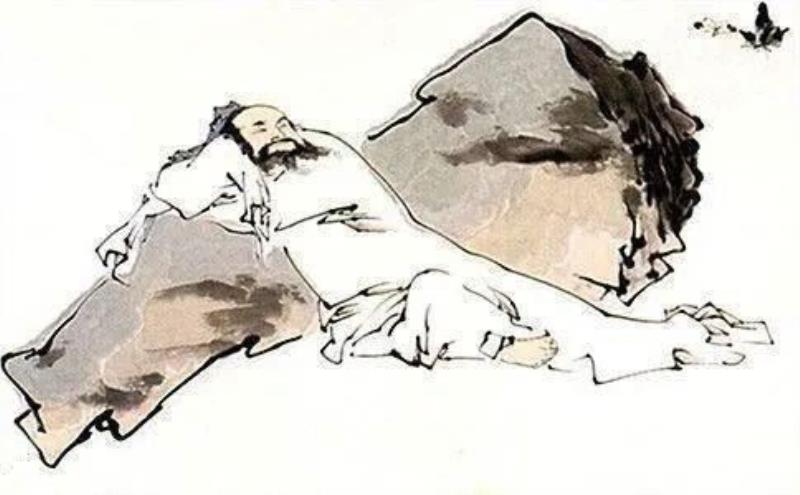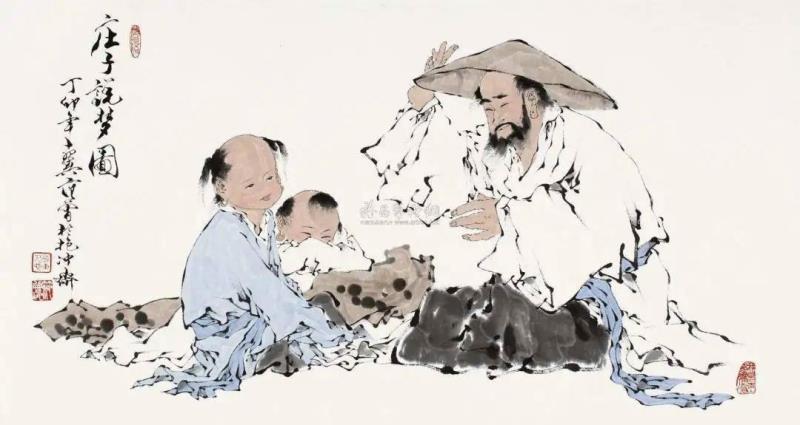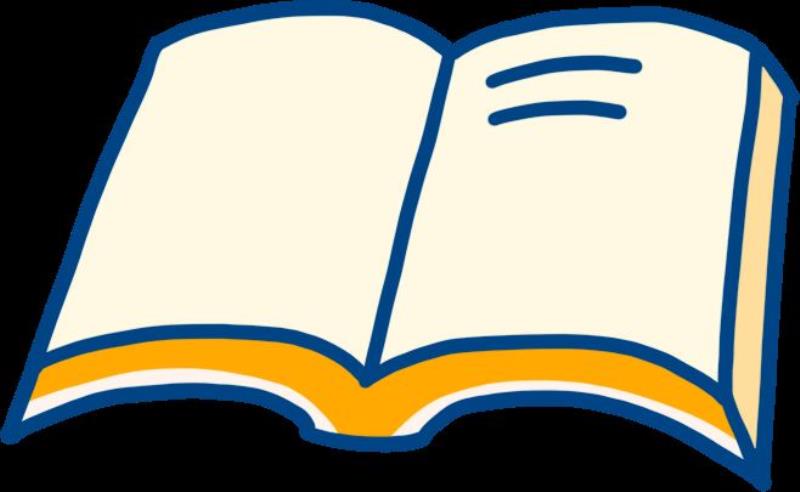編者按
莊子,很多人都知道這個名字
。他留下的《莊子》一書
,將思考和評判融入寓言之中
,通過人物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表達(dá)出自己哲學(xué)的奧義
。在后來的中國思想史上
,幾乎沒有思想家能夠擺脫莊子的影響
。那么普通的哲學(xué)愛好者
,該如何進(jìn)入莊子的著述與思想?如何理解莊子的文章之美
?以下是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楊立華在北大博雅講壇《中國哲學(xué)十五講》直播活動中的演講
。
《莊子》之美在“莊周夢蝶”里,但非大手筆不能為的卻是這部
作者/楊立華
整理/周丹旎
莊子的著述和思想,對于我來說非常重要
,我自己走進(jìn)哲學(xué)之門
,走上哲學(xué)研究的道路,最初引路的書就是《莊子》
。在我大學(xué)三年級的時候
,偶然一個機(jī)會接觸到了《莊子》,從此欲罷不能
,于是就考了北大哲學(xué)系的研究生
,開始跟隨老師們學(xué)習(xí)。多年來
,我的研究脈絡(luò)一直沒有離開過莊子
,過去一年多也一直在圍繞莊子進(jìn)行研究和寫作。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莊子》閱讀和思考的心得
。
如何理解“非大哲學(xué)家不能解莊”
歷來對《莊子》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有的是更學(xué)院派的研究
,有的是更偏向于去領(lǐng)會其中的人生實踐智慧的寫作
,這些寫作也是根源于這樣偉大的哲學(xué)家所留下的思想或者精神性的文本,它們都很重要
。除了學(xué)院派研究、傾向于人生實踐智慧方面的寫作
, 《莊子》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研究脈絡(luò)
,就是注疏的脈絡(luò),即詳細(xì)注解
、解釋
、逐字逐句逐章地解讀《莊子》全書。在我看來
,我們要想了解古代偉大哲學(xué)家的思考
,除了研讀他留下的文本以外,我們沒有別的東西
。尤其是像莊子這樣的人
,其實關(guān)于他的歷史記載非常少,我們能夠做的其實不過就是“讀其書
,想見其為人”而已
。至于他的生平,他是什么樣的人
,他的人生經(jīng)歷如何
,除了書里面留下來的印跡之外,別的我們都不知道。

注釋《莊子》的作品非常多
。在我念研究生階段
,剛剛著手讀《莊子》的時候,陳鼓應(yīng)先生的《莊子今注今譯》對我影響很大
,這是我自己閱讀《莊子》時比較早的淵源
。其實,讀《莊子》還有一些注疏類的作品是繞不過去的
。例如
,鐘泰的《莊子發(fā)微》對《莊子》的文本解讀非常細(xì)致深入。不過我個人認(rèn)為
,儒家和墨家是可以稱作學(xué)派的
,因為其既有思想傳承,又有明確的傳承屬性
。 但道家不同
,它沒有明確的傳承譜系,這個跟儒家
、墨家相差非常遠(yuǎn)
。所以說“以老解莊”是我不能贊同的,在我看來
,
老子與莊子的哲學(xué)主題
、思想宗旨和哲學(xué)關(guān)切點是有根本區(qū)別的。
其實“解莊”非常難
,難就難在《莊子》的文本
。《莊子》沒有一個明確的口傳傳統(tǒng)
。舉個例子
,讀《論語》或者《孟子》,特別是《論語》
,和它相關(guān)的解釋傳承
,幾乎一直都沒斷過。正因為它有口傳的傳統(tǒng)
,所以《論語》不管有多少種解釋
,其解釋都有統(tǒng)一性,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是大家不會去質(zhì)疑的
。但是《莊子》不一樣
,《莊子》文本本身就很龐雜
,再加上到了魏晉時期
,它才受到普遍的重視,開始有了比較多的注釋
。特別是郭象把《莊子》的文本進(jìn)行重新整理,并加以注釋
,我們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莊子》文本才確定下來
。 這就導(dǎo)致了莊子的哲學(xué)有一個非常長的歷史隔斷。所以
,不管哪一代研讀《莊子》的哲學(xué)家
,他都只能面對手里的文本去跟這個哲學(xué)家對話。
我有一個說法:非大哲學(xué)家是不能解莊的
。你沒有那種思考能力
,無論你有多深的訓(xùn)詁功夫都沒有用,必須要有根本的
、足夠深的哲學(xué)思考
,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你才能“碰見”那個哲學(xué)家
。所以
,對于《莊子》這種沒有口傳傳統(tǒng)、有歷史隔斷的經(jīng)典文本
,真的需要有哲學(xué)心靈的人才能解
。在《莊子》的注疏脈絡(luò)當(dāng)中,有一本非常了不起的書
,就是王夫之的《莊子解》
。王夫之的《莊子解》好在哪里?王夫之本人就是大哲學(xué)家
,在那樣的哲學(xué)高度上
,他能在對話關(guān)系里不時地透射到莊子偉大的哲學(xué)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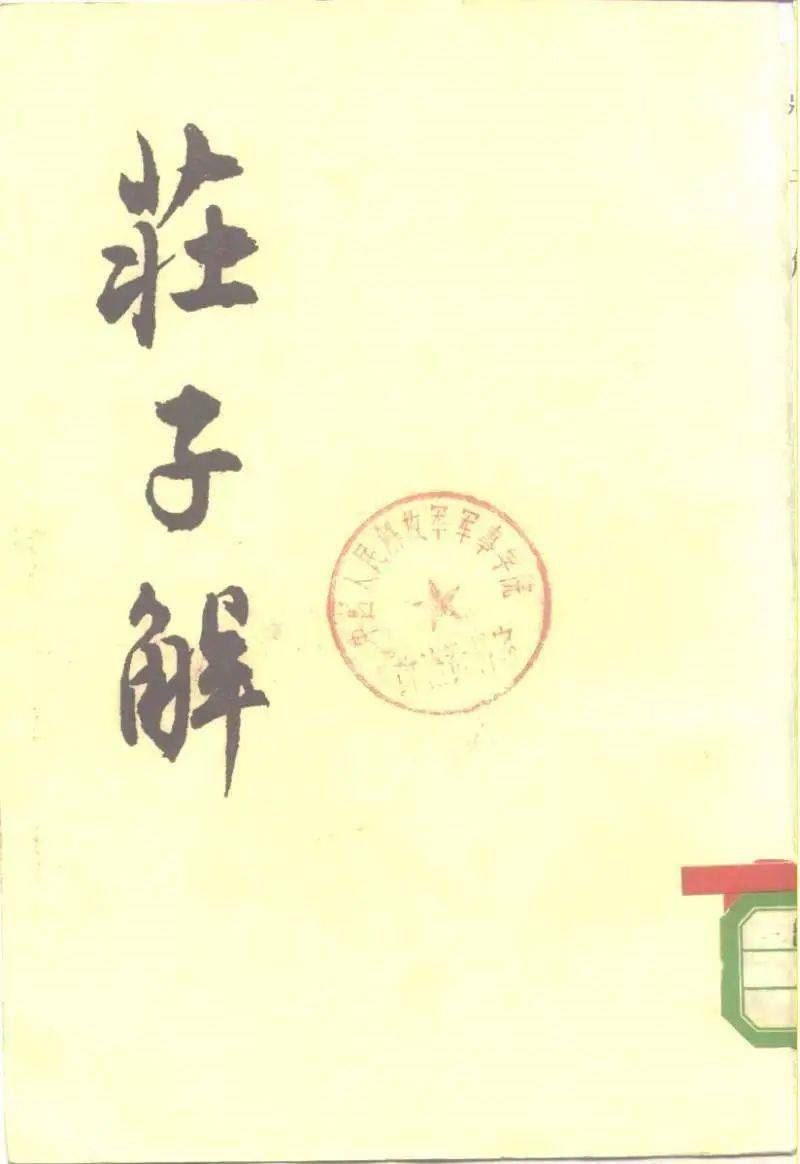
朱子注《四書章句集注》時有一個特別清晰的理念: 注的內(nèi)容不要太多
,不要用自己的注湮沒了經(jīng)典本文,經(jīng)典本文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朱子作為一個大哲學(xué)家
,也是一個文學(xué)家的清晰認(rèn)識。不管我的文字多重要
,不管我的解釋多細(xì)致
,都不能遮蓋了經(jīng)典本文。錢穆先生在他的《莊子纂箋》中
,也貫徹了朱子的這一理念
。錢先生廣泛搜集資料,把他認(rèn)為重要的都匯集在一塊
,既不失簡明
,又很廣博豐贍
。
最后,歷代《莊子》的讀者繞不過去的就是郭象
,因為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
,嚴(yán)格意義上講是經(jīng)過郭象整理之后的《莊子》。盡管郭象注可能在很多地方明顯地曲解了《莊子》原文的意思
,但如果我們真正地讀進(jìn)去
,深入地理解郭象的注釋,把他的注釋作為哲學(xué)經(jīng)典去讀
,你會發(fā)現(xiàn)他在很多地方確實有深契于《莊子》哲學(xué)的地方
。深契《莊子》哲學(xué)的地方, 那就是哲學(xué)的對話
,是一個偉大哲學(xué)家向另一個偉大哲學(xué)家的致敬
,他們以這樣的方式相互致敬和相互質(zhì)疑。
《莊子》并非都是其本人所作 ?
《漢書·藝文志》里面著錄的《莊子》是52篇
,而我們今天看到的《莊子》是33篇。33篇文本的《莊子》
,分為“內(nèi)
、外、雜”三個部分
,其中“內(nèi)篇”7篇
,“外篇”15篇,“雜篇”11篇
。它比《漢書·藝文志》里著錄的52篇版《莊子》篇幅少了40%
。是怎么少的?這是郭象做的刪削整理
。因為郭象發(fā)現(xiàn)
,他原本看到的《莊子》的“外篇”“雜篇”里龐雜的東西太多,用郭象的話說“或類《山海經(jīng)》
,或類《占夢書》”
。在他看來,這樣的東西不可能是莊子作為一個哲學(xué)家所留下的文本
,所以他就把這個部分刪掉了
,并且對“外、雜篇”剩下來的篇章做了整理歸類
。
“內(nèi)篇”7篇
,“外篇”15篇,“雜篇”11篇
,“內(nèi)
、外
、雜”哪個部分是莊子本人作的?或者全都是莊子本人寫的
?蘇東坡熟讀《莊子》之后認(rèn)為
,至少有四篇絕非莊子本人所著:“說劍”“讓王”“盜跖”“漁父”。 王夫之在《莊子解》里明確講“外篇”15篇全都不是莊子作的
,他說這是“后世學(xué)莊者為之”
,這是了不起的見識。他為什么這樣看
?因為他本身就是文體家
,他看出來莊子的文章不是那么寫的。王夫之評價其中一篇
,說文字“軟美膚俗”
,這個文字怎么可能是莊子寫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
,到底“內(nèi)篇”是莊子本人所作
,還是“外、雜篇”是莊子本人所作
?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
,大部分學(xué)者都認(rèn)為“內(nèi)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而“外
、雜篇”不是
。但即使持這樣觀點的人,也并沒有特別充分的根據(jù)
。拿不出充分的理由
,提不出明確的根據(jù),你的講法只能是主觀的
。王夫之本人是文體大家
,他對文章的感覺是非常個體化的,這種感覺是無法傳達(dá)給我們的
,沒有辦法作為有效的證據(jù)來說
。雖然歷史上認(rèn)為“外、雜篇”是莊子本人所作
,“內(nèi)篇”不是的學(xué)者居少數(shù),但畢竟有
,而且是一些大學(xué)者
。在這派當(dāng)中,影響最大的應(yīng)該是任繼愈
。 任公一直都在講“外
、雜篇”是莊子本人所作
,而“內(nèi)篇”不是。他的根據(jù)是《史記》
,司馬遷為莊周作傳
,并引用了《莊子》的話。任公注意到
,司馬遷引的莊子的話或者篇名
,都是“外、雜篇”的
。由此他認(rèn)為
,這意味著在司馬遷看來,“外
、雜篇”肯定是莊子本人的作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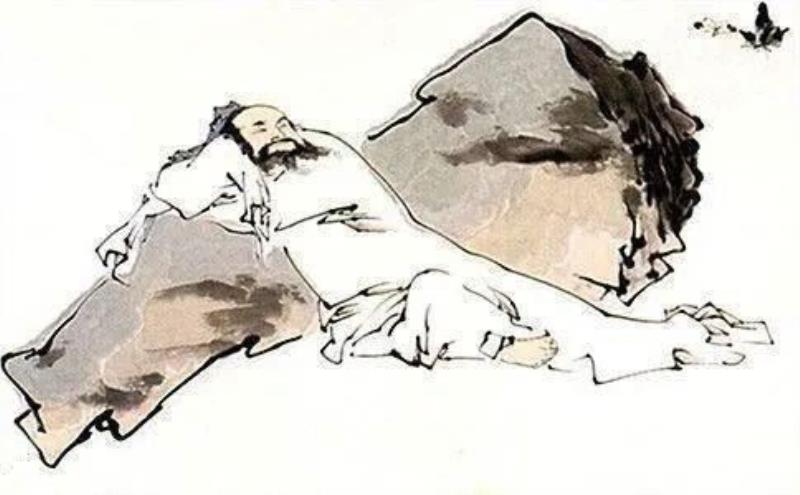
不得不說這個證據(jù)我們無法輕視,因為無論如何
,我們離《莊子》都比司馬遷離《莊子》遠(yuǎn)太多
,司馬遷距離《莊子》的時代更近,他能看到的資料肯定比我們看到的資料更多
。他如果認(rèn)為“外
、雜篇”是莊子本人的作品,而“內(nèi)篇”不是
,這是不能輕視的
。雖然大多數(shù)學(xué)者不贊成這個意見,但也找不到確切的反駁證據(jù)
。
20世紀(jì)80年代初
,現(xiàn)在北京師范大學(xué)的劉笑敢教授,曾在其博士論文《莊子哲學(xué)及其演變》的開頭部分做了非常詳盡的考證
,基本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他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按照漢語的發(fā)展,單字詞的出現(xiàn)
,一定是早于雙字詞
,一定先有單字,然后再有組合字
。他注意到幾對概念:“精神”“道德”“性命”
,這里面特別突出的是“精神” “道德”,在“內(nèi)篇”里
,“精”“神”和“道”“德”沒有出現(xiàn)連用的情況
。“外
、雜篇”里開始頻繁出現(xiàn)它們的連用
,有人反駁說連用也不是作為完整的一個詞
,也是在講“精”和“神”,“道”和“德”
。但有連用的情況和沒有連用的情況就是大的問題
,特別是當(dāng)“精”“神”連用的時候,你一定要說這個詞不是一個單一的詞
,這個要結(jié)合上下文仔細(xì)去讀
。《天下》篇講莊子“與天地精神獨往來”
,“天地精神”當(dāng)然是連在一塊的
,是一個完整的詞。 所以一旦明白這一點之后
,就能夠證明一件事
,“內(nèi)七篇”整體上早于“外、雜篇”
。通過這個線索還能夠確定年代
,把《莊子》和同一時代的、早于《莊子》時代的經(jīng)典加以比較
,會發(fā)現(xiàn):跟《莊子》同一時代的
,比如《孟子》,還有早于《莊子》時代的
,比如《論語》
,里面都沒有“道德”“精神”“性命”連用的情況。而偏晚的經(jīng)典
,比如《荀子》《韓非子》就已經(jīng)開始頻繁出現(xiàn)這些詞的連用
。由此可以基本確定,整體上講“內(nèi)七篇”早于“外
、雜篇”
。
劉老師還特別做了統(tǒng)計, 通過統(tǒng)計可以看到
,《莊子》“內(nèi)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頻率極高
,這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內(nèi)七篇”的整體性。而且和《孟子》相對比
,我們發(fā)現(xiàn)《孟子》也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基本可以確定《莊子》“內(nèi)七篇”和《孟子》是同一時代的文本。 而根據(jù)歷史記載
,孟子和莊子恰恰就是同一個時代的
,他們恰好都是梁惠王、齊宣王時代的人。

《莊子》之美不僅在于“莊周夢蝶”
《莊子》這本書真正的研讀重點
,我個人認(rèn)為當(dāng)然是“內(nèi)七篇”。但不是說“外
、雜篇”不應(yīng)該讀
,“外、雜篇”是后世學(xué)莊者所為之
,某種意義上也是后世學(xué)莊者對“內(nèi)七篇”的理解
。因為這里面匯集的文獻(xiàn)篇章離莊子都很近,所以里面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信息
,對于我們理解莊子是很重要的
。而且由于是后世學(xué)莊者,對莊子的某些思想片段有充分的發(fā)揮和展現(xiàn)
,所以有些篇章也很妙
。
很多人以為《莊子》之美在“莊周夢蝶”里。其實要真正去體會《莊子》文章之美
,不要光看“庖丁解?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薄扒f周夢蝶”。 《莊子》文章里最難寫的是什么地方
?非大手筆不能為的是哪部
?是《人間世》。尤其是《人間世》第一章
,要編出一段顏回和孔子之間的對話
,而且顏回每次說的話,在孔子的提點之下還要不斷提高
。既要符合顏回的思想
,符合他的個性,還得能夠在孔子引導(dǎo)之下不斷提高
,這是非常難寫的
。所以,如果莊子今天還活著
,那絕對是一個偉大的編劇
,什么細(xì)節(jié)都要注意到,絕對不帶穿幫的
。當(dāng)然也有個別馬腳被我們發(fā)現(xiàn)
,比如莊子特別喜歡“十九”這個數(shù)字。庖丁那把刀用了十九年
;《德充符》里“吾與夫子游十九年
,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也是十九年。為什么都是十九年呢
?因為你說十一年太少
,說二十年太整齊了,就十九年像真的
。時間又足夠久
,接近二十,又不是十八
、二十這樣的整數(shù)
,所以這個數(shù)字看起來像真的。
但是莊子為什么采取這樣的寫作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