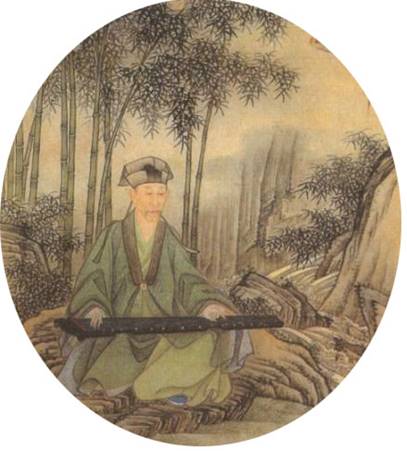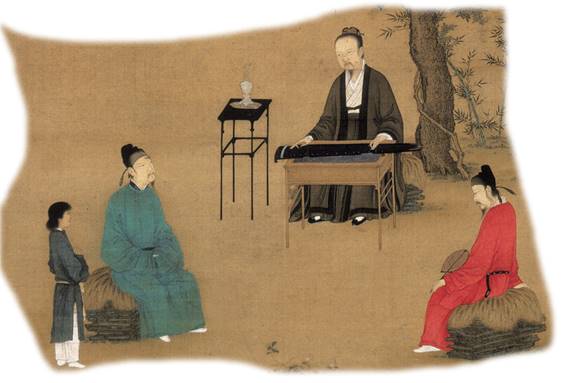韓吉紹
|
坐觀天地遠見遐 ,忽然萬里渡江河。以龍為馬云為車,時入天門見大家 。
|
引 言
《黃帝九鼎神丹經(jīng)》(以下簡稱《九鼎丹經(jīng)》),現(xiàn)存文獻最早見于晉葛洪(83-363)《抱樸子內篇》著錄引用 。關于此書的來歷,葛洪如是說:“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
,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jīng)
,會漢末亂
,不遑合作
,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
。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
。凡受《太清丹經(jīng)》三卷及《九鼎丹經(jīng)》一卷、《金液丹經(jīng)》一卷
。余師鄭君者
,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
,又于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
。余親事之
,灑掃積久,乃于馬跡山中立壇盟受之
,并諸口訣訣之不書者
。江東先無此書
,書出于左元放
,元放以授余從祖
,從祖以授鄭君
,鄭君以授余
,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
。”葛洪又云該書另有祭圖法
1卷。根據(jù)葛洪所述,九鼎丹與太清丹、金液丹乃中國煉丹術早期最重要的三種大丹法。

華夏道祖——軒轅黃帝
九鼎丹托名于黃帝,系匯總漢代頗為流行的黃帝鑄鼎于荊山而仙去的傳說。據(jù)《史記》
記載,漢武帝時齊地方士公孫卿云:“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余人,龍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既托名于黃帝,表明該丹法具有至高地位?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吨芤讌⑼酢吩峒熬哦Φぃ疲骸拔┪羰ベt
,懷玄抱真
,服煉九鼎
,化跡隱淪
,含精養(yǎng)神
,通德三光
?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蔽宕頃宰⒃唬骸拔汗^三皇修九鼎丹而服食
,致含精養(yǎng)神
,通德三光,化淪無形
,以為神仙
,賓于上帝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彼侮愶@微更云:“魏君慮世人不達,故又指古之圣賢懷玄抱真
,莫不服食九鼎
,通德三光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绷禾蘸刖埃?/span>
56-536)欲煉丹,所舉丹法之首即“黃帝九鼎九丹”
。

然而,葛洪之后《九鼎丹經(jīng)》并未得到廣泛流傳
,其丹法知之者寡
。至中唐,梅彪甚至認為它已經(jīng)失傳,《石藥爾雅》(撰于
806年)卷下“論諸大仙丹有名無法者”位列其首的便是黃帝九鼎丹。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事實上,從南北朝至唐,九鼎丹法一直流傳不絕。如《太平御覽》卷671引《登真隱訣》,述太極真人九轉還丹法,其中提到九鼎丹,云“昔黃帝火九鼎于荊山
,《太清中經(jīng)》亦有九鼎丹法”
。陶弘景在茅山建藥屋靜院時甚至發(fā)現(xiàn)了前人合九鼎丹的遺物:“《登真隱訣》云:昔李明于此下合九鼎丹以外玄洲
,發(fā)掘基址
,屢得破瓦器
,乃其舊用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span>
又如孫思邈(約581-682)《太清丹經(jīng)要訣·諸丹目錄三品》記神仙出世大丹異名13種,其首即為黃帝九鼎丹,并說:“右諸大丹等
,非世人所能知之。今復標題其名
,記斯篇目,而終始不可速值也
,是以其間營構方法
,并不陳附此。其有好事者
,但知其大略也?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贝送?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還有少數(shù)丹經(jīng)引述過《九鼎丹經(jīng)》的內容
。
總之,盡管九鼎丹是所謂“非世人所能知之”而流傳不廣的大丹,但其丹法并口訣還是被載于典籍流傳下來
,《正統(tǒng)
道藏》便保存有兩種九鼎丹文獻 ,一為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jīng)》 ,二為
《黃帝九鼎神丹經(jīng)訣》 ,以下分別論之。

一、《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jīng)》與九鼎丹法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jīng)》(以下簡稱《流珠經(jīng)》),
2卷,題太清真人述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锻ㄖ尽に囄穆浴分?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作二卷
,但不題作者
。唐代道經(jīng)《道典論》卷
4有引述,作《真人流珠九轉神仙九丹經(jīng)》,其文云:
“真人曰:服九丹令人神仙度世,長生久視,長服之壽萬世。九丹者
,九道也
,九方也
,治之各自有道
,治九丹凡一法也
。第一之丹名華丹
,第二之丹名神符丹
,第三之丹名神丹
,第四之丹名還丹
,第五之丹名餌丹,第六之丹名宜丹
,第七之丹名深丹,第八之丹名伏丹
,第九之丹名寒丹也。
”
另一部年代不明的道經(jīng)《上清道寶經(jīng)》云:“九丹者 ,九道,如九方也
,服之壽萬世
。第一丹名九華
,第二神符
,第三龍丹
,第四還丹
,五餌丹,六瑓丹
,七深丹,八伏丹
,九寒丹
。真人流珠九轉神仙九丹經(jīng)
。
”
以上二書所記九丹名稱與《流珠經(jīng)》不盡相同,后者“眶”字闕筆
,知其源于宋本
。
《流珠經(jīng)》的內容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為卷上前闕九丹歌文,第二為歌文注釋
,第三為九丹作法及功效
,第四為卷下篇末所附諸神仙方(包括餌雄黃方
、真人神水法
、合藥用仙人鳳綱法
、呂恭起死方、采服芝法
、淮南神仙方),其中第二
、三部分混合在一起
,第四部分與前三部分無直接關系
。
經(jīng)中九丹名稱分別為丹華、神符、神丹、還丹 、餌丹
、煉丹
、柔丹
、伏丹、寒丹
,與葛洪所言九丹名稱完全相同
。該經(jīng)卷下云:“九鼎者
,九丹也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庇帧饵S帝九鼎神丹經(jīng)訣》卷
12云 ,黃帝九鼎神丹第一之法名曰丹華
,復有一名號曰流珠九轉
。同書卷
20引《九鼎丹隱文訣》云,九丹第一之丹有二名,一名流珠九轉,二名丹華。根據(jù)以上信息可以斷定,《流珠經(jīng)》所述九轉流珠丹法即九鼎丹法。

《流珠經(jīng)》的編撰年代不甚明確。陳國符根據(jù)九丹中第一、二、三、六丹及總論之歌文,認為其用韻有兩漢例,有東漢例,有西漢例,故斷定歌文當于西漢末東漢初出世。又據(jù)經(jīng)中“解曰”一段所用四地名滎陽、河南、洛陽及穎川郡的設置時代,認為此解乃西漢至隋代人所撰,具體不能確定。
孟乃昌則認為,歌文撰寫應在《神農本草經(jīng)》之后、《本草經(jīng)集注》之前,注文則較陶弘景為晚。關于《流珠經(jīng)》中歌文的出世時代我們留待下文再討論,這里先分析《流珠經(jīng)》的編撰時代
。
《流珠經(jīng)》題太清真人述。又經(jīng)中有“三五”之名(
磁石、鉛屬太陰
,位在子
,其數(shù)一
;丹砂屬陽
,位在午
,其數(shù)九
;雄黃屬土
,其數(shù)五
。故曰一五九
,凡十五
,故真人名為三五
),此隱名見于《抱樸子內篇》所引《太清丹經(jīng)》而不是《九鼎丹經(jīng)》:“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以上兩點皆表明《流珠經(jīng)》與太清經(jīng)傳統(tǒng)有關,反映出該經(jīng)編撰時代較晚,因為九鼎丹法與太清丹法在葛洪時尚涇渭分明,其后二者關系漸趨復雜,出現(xiàn)九鼎丹法摻雜太清丹法的現(xiàn)象(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見下文)。至于更具體的判斷依據(jù),仍需從地名入手來尋找。
《流珠經(jīng)》歌文注釋和丹法部分提到的地名不多,如第一丹“解曰”中的“土釜滎陽
、河南
、洛陽及潁川郡者”
,以及第三丹的“真雄黃
、雌黃皆出正陽武都
,武陽亦有雄黃”
。按武陽出雄黃未見他處記載
,此地名在唐前出現(xiàn)多次
,根據(jù)中古以前雄黃的出產地域推斷
,此武陽當為西魏所置武陽郡
,屬武州
,治所在葭蘆縣(今甘肅武都縣東南
70里白龍江東岸),北周時郡縣并廢
。而此武都當為西魏所置武都郡
,同屬武州
,治所在石門縣(今甘肅武都縣西北
40里石門鄉(xiāng),一說在今武都縣東南)
,北周改為永都郡
。
至于“解曰”中的滎陽、河南、洛陽及潁川亦當為同時期郡名,全都位于北方地區(qū),與《抱樸子內篇》惟云南方土釜同理,皆源于南北分割之故。根據(jù)以上地名分析推測
,《流珠經(jīng)》應撰于西魏時北方地區(qū)?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有《真人九丹經(jīng)》
1卷,疑即此書原本
。

至于《流珠經(jīng)》卷下所附諸神仙方,葛洪與陶弘景多有引述
,可知其淵源較古
。如
餌雄黃方在《抱樸子內篇·仙藥》中的雄黃餌服法中有提及,但系本經(jīng)方法的概括
。
合藥用仙人鳳綱法在葛洪《神仙傳》有記載,內容為本經(jīng)法之節(jié)略
。呂恭之事亦見《神仙傳》
,但內容不同
。此方中有“桂三種者”一句
,按《本草經(jīng)集注》桂條云:“案《本經(jīng)》唯有菌桂
、牡桂
,而無此桂
,用體大同小異
,今世用便有三種
,以半卷多脂者單名桂
,入藥最多
,所用悉與前說相應?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断山?jīng)》
乃并有三種桂,常服食 ,以蔥涕合和云母蒸化為水者
,正是此種爾?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庇志饤l云:“《仙經(jīng)》乃有用菌桂,云三重者良
,則判非今桂矣,必當別是一物
,應更研訪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睋?jù)此疑“三種”可能為“三重”之誤
。
采服芝法部分內容同《抱樸子內篇·仙藥》記載。
淮南神仙方中的陳永伯之事見葛洪《神仙傳》,惟文字略有差異
。本經(jīng)云生地黃出渭城
,而《本草經(jīng)集注》干地黃條陶注曰:“生渭城者乃有子實
,實如小麥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茨掀呔⒂弥?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被茨贤跗呔?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即本經(jīng)之淮南神仙方
。
《流珠經(jīng)》九丹歌文注釋詳略不一,且部分歌文或與注釋混淆難以區(qū)分,或無注釋,因此已無法完全恢復歌文原貌。今在陳國符工作的基礎上,將明顯為歌文的句子摘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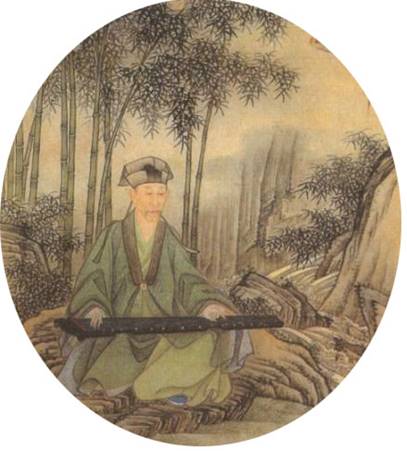
……婚親多。道士持戒游五都 。其子四千金銀加。子明炊婦與赤爐
。用口牙如黃真多
。蒸覆柔筒中如巴
。子明惶悸內懷河
。鄰里雄黃及丹砂。轉相和解謝其家
。牡蠣赤石使不邪
。雪霜紫色若蔥華。后乃相聽兩性和
。日暮腸動應感加
。夫妻共戲色忽華。陰陽以會樂不過
。即日生子如積沙。銅羽次藥土龍和
。化金銀……水……一斤一銖慎無多
。食如黍粟飛相過
。坐知天地遠見他
。忽然萬里渡江河
。以龍為馬云為車
。時入天門見大家
。身比日月在欲何
。盡見賢圣相對羅
。靈龜駢鵝神蝦蟆
。伯牙鼓琴玉女歌
。青腰起舞悲相和。但獨煩冤當奈何
。身遂服食神丹華。邪氣不害疾不過
。幸得度世吉無他
。
真人曰:第二之丹名神符。本生太陽河伯余。其子四千相與俱。河上姹女誠獨姝。娥眉白易如明珠。長沙好砂色由由。少小貞信不用夫。東西南北父母俱。身不玷污清若珠。好待賢士相待須 。勇悍敢語言若書
。安心懷能才有余
。不校人女妄吹噓
。子明媒之使共居
。與不相聽欲上書
。后復會面神丈夫。子明迫之用赤釜
。后竟相聽色由由。四時生子若神廬
。五色光顏厚寸余。和以黃戍復如初……以行水上足不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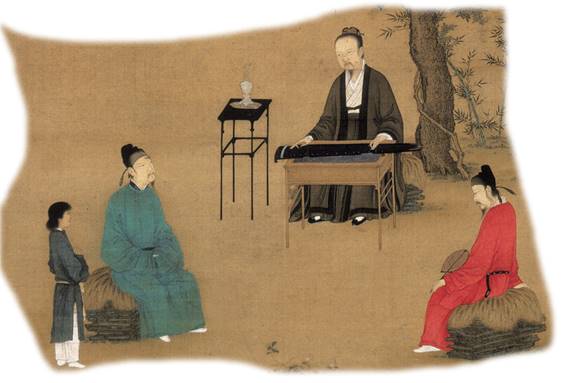
真人曰:第三之丹名神丹。五色參差誠可觀。本自正陽武都間。潔凈白面又大神。常得賢士兩萬錢。面色較好□目燔。晨昏夜暮止名山。方士劫之不敢焉。取下土石……服之系之皆大神。子明合會使相親。雄雌合得火飛精。善涂其際致令堅。取上飛雄雌黃精。和以龍膏物相因。食之不死壽萬年。坐使諸神……奴婢雞狗皆可仙。凡人服藥亦皆然……常居石室依名山。能得神丹皆升天。百官雞犬青云間。世皆歷盛去甚難。
真人曰:第四之丹名還丹。男子兄弟通九人……
真人曰:第五之丹名曰餌丹。本自長沙武陵士
。太一旬石朱氏子。子明媒之與賢士
。……神爵子
。……服之不久三旬日
。萬神侍從皆事已。玉女青腰皆可使
。
真人曰:第六之丹名煉丹。所出微妙諸神仙。乃出蠻夷巴越間。目如珠光口如丹。賢者不取人民間。飛流八石三旬間。子明和調令可丸。小火以泥涂釜際。八石當飛如雪霜。和以龍膏物相因。亦可服食黃白成。諸神敬諾聽己言……女子服之亦飛仙……作藥不食糖苦捐。如身涂污去之難。
真人曰:第七之丹名柔丹。圣人齋戒成大神。當求河女以為姻。與鉛合精作金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