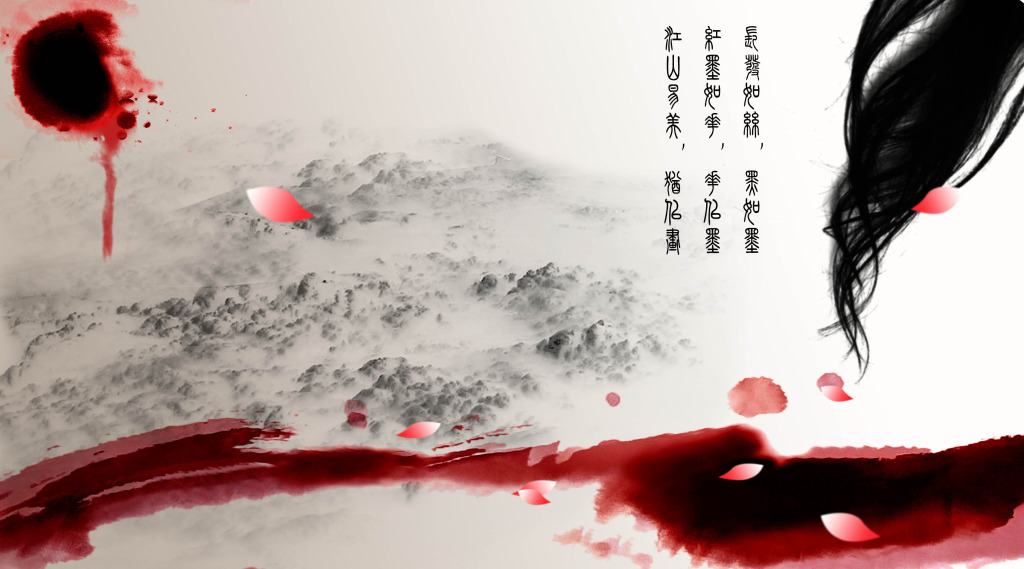匡釗
道家內(nèi)丹
明清會道門對于來自道教的內(nèi)丹修煉思想與技術(shù)的繼承早已為研究者所注意,“在民間宗教中,修
煉內(nèi)丹成為一種普遍的宗教內(nèi)容……道教修煉內(nèi)丹的理論和實踐在民間宗教這里被改頭換面而且通俗化 、普及化了
”。
這種修煉,被會道門中的實踐者形象地稱為“坐功運氣”
。道教的內(nèi)丹修
煉,其蛛絲馬跡最早可以回溯到先秦,比如戰(zhàn)國時代的《行氣銘》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卻谷食氣》都可被認為包含了內(nèi)丹思想的早期萌芽,至于時代較早的道教經(jīng)典,像《抱樸子》《黃庭經(jīng)》之類,其中已經(jīng)存在清晰的關(guān)于存思、服氣與導(dǎo)引的初步理論。但早期道教對于長生的追求,主要是以“金丹大藥”為主,內(nèi)丹修
煉尚非主流,直到唐代外丹吃死大量身份高貴的
煉養(yǎng)者之后,明顯安全的內(nèi)丹,便在后來全真派等新興道教流派中成為個體修
煉的主要方式。這個道教內(nèi)部內(nèi)丹修
煉譜系,應(yīng)該說早已為眾多研究者所熟知,而如果說各種明清之際的會道門都與道教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它們共享來自正統(tǒng)道教內(nèi)部的諸多因素,那么此種類型的修
煉,也不會不滲透到官方認可的道教團體之外的鄉(xiāng)民組織中,只是后者對于
內(nèi)丹修煉的挪用,其意義遠非從思想理論或個體實踐的繼承角度便能窮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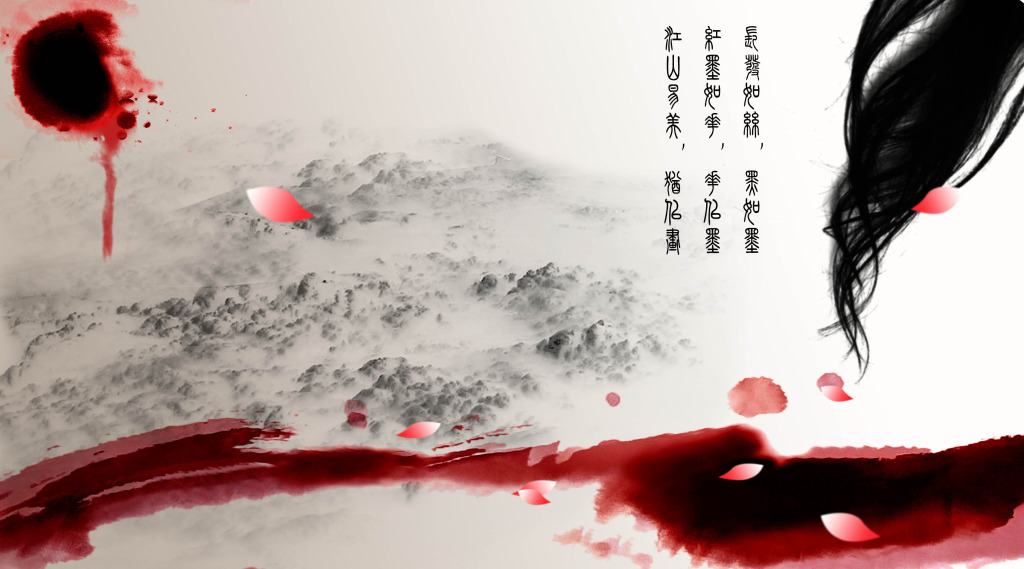
對于 明清會道門中內(nèi)丹術(shù)的普遍流行的直接了解,可以會道門中流傳的各種“寶卷”為基本材料
。“作為民間宗教教義的‘寶卷’
,包含著豐富而龐雜的
煉養(yǎng)思想,成為道教影響下層民眾的中介物之一?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眴栠@條線索起始于明代初年
,“明初《佛說皇極結(jié)果寶卷》是現(xiàn)存最早的民間宗教經(jīng)卷”,雖然尚難斷定其門派歸屬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名詞術(shù)語與道教頗有不同,但修
煉內(nèi)容明顯受著丹道的啟示緊隨其后,與內(nèi)丹相關(guān)的術(shù)語與實踐,基本在所有較為重要的明清會道門中都能發(fā)現(xiàn)蹤跡。
在時間上最早出現(xiàn)的羅教當中,內(nèi)丹一開始是一個被排斥的話題,其始祖“羅祖”夢鴻的思想本來含有反對內(nèi)丹修煉的因素,但這種狀況在羅教隨后的傳播當中迅速得到改變。到了其直傳弟子大寧,便在他自己所創(chuàng)制的寶卷《明宗孝義達本寶卷》中,摻入了內(nèi)丹修煉的內(nèi)容,如其第十四品有言:“權(quán)借此色身為爐,勇猛精進為火,將一切種性頑心為砂為藥
,以智火鍛成一片
,
煉就萬劫不壞圓明真性?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比绻f大寧的涉及內(nèi)丹修煉的話語仍然帶有修辭的色彩,其所欲陳述的對象仍然是心性之類,那么發(fā)展到羅祖再傳弟子秦洞山
,其所撰的《無為了義寶卷》(《佛說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寶卷》)便已經(jīng)不再遮遮掩掩
,明確增加了純粹的修
煉內(nèi)丹的內(nèi)容,拋開心性之類的對象,而將“長生舍利子”、“玉液金丹”作為談?wù)摰膶ο蟆?/span>

此種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在羅教傳人孫真空那里同樣非常明顯,在其所著《銷釋真空掃心寶卷》中,他“與羅清對
煉內(nèi)丹、修長生等道教功夫一再否定的態(tài)度不同……強調(diào)吸陰陽瑞氣
、采曰月精華、結(jié)圣胎
、
煉內(nèi)丹的道教方術(shù)。如果說上述羅教中內(nèi)丹術(shù)以一種不可遏止的姿態(tài)涌現(xiàn),那么到了較為晚出的會道門當中
,內(nèi)丹修
煉已經(jīng)被廣泛接受為其教義與活動中某種正式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成分了。

稍晚于羅教,但深受其影響而發(fā)展起來的
黃天教,“從教義到修持方法都得之北宋以后的(道教
)內(nèi)丹派”間,其經(jīng)典《普明如來無為了義寶卷》開篇就可見“晝夜功行,運周天”、“坎離交
、性命合”這樣純粹的內(nèi)丹術(shù)語。此后
,“如果說東大乘教的《皇極經(jīng)》還帶有禪凈與內(nèi)
丹道相兼的特點……那么圓頓教的《古佛天真考證龍華經(jīng)》則純粹是一部內(nèi)丹書了”。如果說“
修煉內(nèi)丹是弓長倡圓頓教的靈魂,那么其寶卷《龍華經(jīng)》(《古佛天真考證龍華經(jīng)》)則堪稱明清會道門內(nèi)丹修煉理論的集大成之作?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span>
《龍華經(jīng)》開經(jīng)偈即有如下言語:“性命和合,打成一片,金木相并
,水火既濟
,坎離交宮?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薄洱埲A經(jīng)?古佛乾坤品》有言:“無生母
,產(chǎn)陰陽……嬰兒姹女。起乳名
,叫
伏羲 ,
女媧真身?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鄙鲜鑫谋局谐霈F(xiàn)的“嬰兒”
、“姥女”都是明確的從外丹燒
煉時代一直傳承到內(nèi)丹修煉時代的術(shù)語,而“坎離交宮”之類的說法,更在內(nèi)丹修
煉的語境中具有清晰的指向。更為重要的是,《龍華經(jīng)》包含一個關(guān)于內(nèi)丹修
煉的相當詳細的“十步功”的說法,其細節(jié)完全是次第分明的內(nèi)丹修
煉之術(shù),對此以往的研究者如馬西沙等、梁景之都有極為詳細的說明
。
至于清代影響極為廣泛的八卦教中,“修
煉內(nèi)丹則是教理的核心”,其教義明確認為,“人人都有‘元妙元’
,都能在體內(nèi)現(xiàn)出‘夜明珠’,即人人都能修
煉內(nèi)丹”。八卦教教首劉佐臣所編《五圣傳道》已經(jīng)將內(nèi)丹修
煉作為教內(nèi)修持的根本追求,“坐功運氣”成為傳授教徒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在《五圣傳道》書中
,同樣出現(xiàn)了大量細致的內(nèi)丹修
煉法門,并頗具創(chuàng)建性地以紡線成布比喻
煉養(yǎng)內(nèi)丹的過程,最終達到“等紡到心花現(xiàn),功業(yè)圓來果也圓”的效果
,“此景即道教所云‘三花聚頂’,‘五氣朝元’
。同樣
,大體同時的聞香教將“修
煉內(nèi)丹的方法謂之‘真道玄機’,把它和三教應(yīng)劫的教理結(jié)合在一起,作為教理的核心,秘不示人”問。聞香教的內(nèi)丹理論,見于其寶卷《九蓮經(jīng)》(《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xiāng)寶卷》) ,
其中明確談?wù)撝敖鸬ご蟮馈?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存氣養(yǎng)神”等話題 ,對于其具體細節(jié)梁景之也已經(jīng)有相應(yīng)研究
。

至于其他會道門,基本上也都同樣關(guān)心內(nèi)丹修煉 ,比如像混元教
、一炷香教、三一教
、黃崖教(太谷學(xué)派)
,直到清末民初還活躍一時的一貫道,其活動與教義中都包含內(nèi)丹術(shù)的因素
。甚至像在理教
、燈花教、真空道等
,這些規(guī)模較小
,重要性也較低的會道門,同樣也講“做功行法”
、“坐功運氣”和“靜坐
” 。
在這些內(nèi)容當中,除了對已知會道門當中內(nèi)丹修煉理論的重復(fù) ,其中某些派別還表現(xiàn)出了一些值得專門說明的特殊之處
。
如一炷香教,也稱“金丹如意道” ,其寶卷《根本經(jīng)》號召信眾:“參禪打坐
,
煉成金丹”。而在相應(yīng)的修煉中 ,此一炷香教中則出現(xiàn)了相當極端的手段
,即所謂“凈身修行”。
宋元以來筆記小說中常有內(nèi)丹修煉者自閹修行的記錄,而在明清會道門當中
,這種方式僅被部分一炷香教徒所效仿,他們對于這種自殘身體的內(nèi)丹術(shù)的接受
,在明清會道門當中是個孤例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三一教與黃崖教這樣以儒家為基底的門派,也都有各自的內(nèi)丹理論,如前者教首林兆恩所發(fā)明與大力提倡主要以其中“艮背法”聞名的“九序心法”,后者則稱其內(nèi)丹術(shù)為“心息相依,轉(zhuǎn)識成智”的“圣功”,其修煉的最終目標仍被帶有儒家色彩的言語所陳述,即達到“貫通古今”、“歷萬劫不滅”的“真心”或“我之心”,在這個意義上,黃崖教的內(nèi)丹修煉又在一定程度上退化為訴諸修辭的意味,這不外是其對于自身原始的儒家學(xué)術(shù)立場的讓步。直到清末大行其道的一貫道,創(chuàng)始人王覺一吸引門徒的手段之一也是內(nèi)丹術(shù),據(jù)說他掌握某種所謂“水升火降”的“九節(jié)功夫”,而后者與圓頓教所謂“十步功”基本一致,講的都是內(nèi)丹修煉的次第。
如果說明清會道門中的內(nèi)丹術(shù),從總體上與道教中同樣的修持方法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此種鄉(xiāng)民組織中間的修煉卻與其在道教系統(tǒng)內(nèi)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有非常重大的不同,而這些不同有的已經(jīng)、有的卻還沒有為以往的研究者所觀察到。我們都已經(jīng)非常熟悉為大多數(shù)明清會道門所共享的那種世界觀與神靈觀。簡單地說 ,前者的核心即是所謂的“三陽劫變”
——粗略而言 ,世界的全部運行過程被分為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三個階段
,其被稱為“青陽”
、“紅陽”與“白陽”三世,分別由燃燈古佛
、釋迦牟尼佛與彌勒佛主宰
,每一世結(jié)束時都會出現(xiàn)影響全世界的災(zāi)難,其中只有少數(shù)特定會道門的信徒才能得到拯救而免于墮落
,最終到“白陽劫”的末尾
,所有被選中的信徒都有機會享受永恒的福祉
——這被稱為“總收元”。至于后者,是以“無生老母”,或者說“無生父母”的崇拜為核心,這位無生老母被認為是天地萬物和人本身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甚至連上述西來三佛,包括中國本土神靈太上老君等,也只是她的代理,而最終末世拯救的權(quán)柄,也掌握在她的手中。
在明清會道門所繪制的這個帶有明顯佛教色彩的世界圖景中,如何平順地引入內(nèi)丹術(shù)并將其結(jié)合為自己教義的一部分實際上并非是毫無困難的。羅教對于內(nèi)丹的早期態(tài)度便很說明問題,道教內(nèi)丹術(shù)的目標是長生不死或者說成仙,而羅教信仰的目標則接近傳統(tǒng)的佛教,著眼于解脫生死。但在明清會道門隨后的發(fā)展中,它們作為中國的特殊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生長出來的混合型的民間信仰,并未單純地遵循任何一種原有宗教的教理教義,以某種表面上相當混亂的方式融合了多種來源的宗教性內(nèi)容。不過這種融合也并非完全沒有理路可循,就來自道教的內(nèi)丹思想而言,明清會道門首先便從創(chuàng)世的角度找到了一個將其融人自身信仰內(nèi)部的結(jié)合點。
這個新擬構(gòu)出來的創(chuàng)世景象,分散地反映在不同的寶卷當中。這個景象本身無甚高明之處,重點在于,寶卷中陳述世界創(chuàng)造的話語,運用著來自內(nèi)丹思想的術(shù)語。創(chuàng)世者無生老母與“嬰兒”、“姥女”一起反復(fù)出現(xiàn)在大量寶卷當中,如前引《龍華經(jīng)?古佛乾坤品》中所謂“無生母,產(chǎn)陰陽……嬰兒姹女”的說法,便是以內(nèi)丹術(shù)語言說無生老母對于世界的創(chuàng)造。類似的言語還出現(xiàn)在《還鄉(xiāng)寶卷》當中,其對創(chuàng)世的描述更為具體:“默運陽中輕清之氣
,鍛
煉一萬八千年……工足結(jié)成嬰姹?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蓖瑯拥囊馑家簿褪恰蹲o國佑民伏縻寶卷?伏魔爺保當今品》中所謂
“采取先天,煉就清氣,一體同觀,任得無生老母
,撒手還元
,成其正覺也?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痹谶@個創(chuàng)世圖景中
,至高無上的無生老母,總是如在《無生老母寶誥》中說的那樣
,“左撫嬰兒
,右攜姹女”而出場
。相當有趣的是,
在道教本來的內(nèi)丹理論當中,原不存在與世界創(chuàng)造有關(guān)語義線索,會道門寶卷挪用內(nèi)丹術(shù)語以陳說此主題,恰與當年周敦頤挪用并逆轉(zhuǎn)陳摶用來表述內(nèi)丹修煉的《無極圖》而為自己表述宇宙創(chuàng)造的《太極圖》相似,而當內(nèi)丹術(shù)語在寶卷當中以相反的程序成為對世界創(chuàng)造過程的合法陳述,這也就意味著對于此種內(nèi)容合法性的委婉接納,我們可以猜測,正是上述將內(nèi)丹術(shù)語挪用為創(chuàng)世陳說的方式,為正面將此內(nèi)容作為信徒修煉的必要部分鋪平了道路。
如果說明清會道門以內(nèi)丹術(shù)的言語來表述其世界觀與神靈觀,這種對于內(nèi)丹思想修辭性的歪曲還不是對其內(nèi)容的直接移植,那么后一種移植最為明顯的成功,則首先展現(xiàn)在反復(fù)出現(xiàn)的會道門內(nèi)丹修煉與醫(yī)療問題的關(guān)系中,而此點也可被作為研究其思想史意義的突破口所在。醫(yī)療技術(shù)在以往早期道教中的地位,在其教團活動初期,可被理解成為吸引更多信眾、樹立宗教領(lǐng)袖權(quán)威和嘗試團結(jié)信眾使其向教團化組織發(fā)展的手段;而在其教團活動的成熟期,則可被理解為已經(jīng)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教團內(nèi)部權(quán)力控制與話語流動的表現(xiàn),其目的更在于鞏固組織的團結(jié)。上述兩種早期道教團體所運用的目的不同的醫(yī)療技術(shù),分別就是被認為具有治療效果的所謂
“符水咒說”與“跪拜首過”間。但在上述這個醫(yī)療技術(shù)在道教中的早期實施情況中,并沒有出現(xiàn)“金丹大藥”
,對于后者的鍛
煉服食,從未被認為對普通疾病具有治療的效果
——這種“高知識含量的產(chǎn)品”一開始就僅僅服務(wù)于使服食者成為不死神仙的更高級的目標。
唐代以后外丹術(shù)的位置為內(nèi)丹所取代,后者成為通向長生久視之路的關(guān)鍵
,但這種取代,卻不是一種忽然出現(xiàn)的“垂直換代”
。遠在此前
,道教或者說道家內(nèi)部早已存在一個內(nèi)丹術(shù)的線索,而這種以“服氣”為主的技術(shù)
,一開始恰是以醫(yī)療為目的的
,早在漢代初年,其就已經(jīng)和“導(dǎo)引”的身體技術(shù)一起服務(wù)于調(diào)節(jié)、強健身體甚至治療疾病
——這可能就是為什么馬王堆出土的帛書里《卻谷食氣》會與《導(dǎo)引圖》和《陰陽十一脈灸法》抄寫、描畫在一起
。
《陰陽十一脈灸法》的內(nèi)容肯定包含著傳統(tǒng)中醫(yī)慣用的醫(yī)療技術(shù),而“服氣”與“導(dǎo)引”被與之并列,顯然暗示它們均有相似的功效
。只是內(nèi)丹術(shù)的這種疾病治療效果,可能要晚至唐代才得到充分的注意
,“
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就以存思日月、存思臟腑、引導(dǎo)
、運氣
,以治療各類疾病
”,不過他所提倡的這種具有醫(yī)療作用的內(nèi)丹術(shù),并不是單純的“食氣”或“服氣”
,而同時結(jié)合了“導(dǎo)引”的要素在內(nèi)
——這等于是綜合了馬王堆帛書中的前兩個相關(guān)項目。在這個理論背景之下,到了宋代的道教,其內(nèi)部的內(nèi)丹術(shù)至少可據(jù)此被認為同時具有髙低兩層次的功能:在較低的層次上,內(nèi)丹術(shù)具有新興的醫(yī)療功能;在較高的層次上,內(nèi)丹修煉仍然通向神仙之道。
但上述兩個層次的顯現(xiàn)未必同樣清晰,往往其中較高的層次對于較低層次有某種遮蔽的作用。
場景轉(zhuǎn)換到明清的會道門中間,上述遮蔽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
,他們從道教那里挪用過來的內(nèi)丹術(shù)所具有的醫(yī)療功能已經(jīng)完全被正式確定為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將各種會道門成員對治病技術(shù)的表述稍加歸類
,可以辨認出其開展的醫(yī)療活動的三種模式:
念經(jīng)、跪香、運氣
。
“念經(jīng)”也就是歷史上“符水咒說”的延續(xù),一般來說念經(jīng)的過程往往同時配合有飲用融合了燒化后紙符的“符水”;“跪香”無疑是以往“跪拜首過”的變體
,而這方面內(nèi)容同時也與一些被冠以“寶懺”書名的寶卷有關(guān)
——這些作品號召會道門信眾通過“懺悔前罪”的方式,達到消災(zāi)除病的效果;至于新興的醫(yī)療技術(shù)“運氣”或者說“坐功運氣”,不外就是“食氣”或“服氣”的通俗說法
——“與念經(jīng)治病不同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