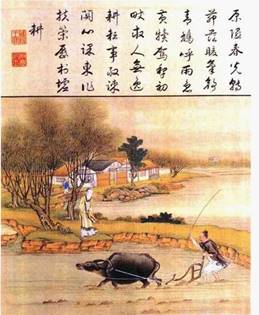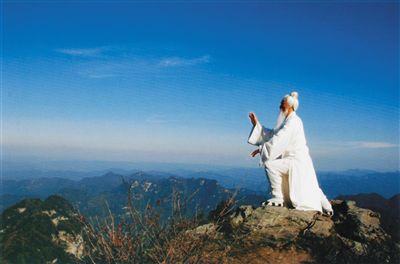李國榮
|
雍正即位后,極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師張伯端,封其為“大慈園通禪仙紫陽真人”,并軟命在張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觀以崇祀。據(jù)《紫陽道院碑文》載,雍正特別贊賞真人張伯端“發(fā)明金丹之要” 。
|
雍正是清朝諸帝中崇奉道教最為突出的一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服食外丹的帝王。
丹道這一杰出的道學(xué)文化對雍正其人影響甚大,很值得研究。
一、以驅(qū)邪治化為功用的仙道崇好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
它以戰(zhàn)國時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為根基,兼融我國古代流傳的巫術(shù)禁忌、
鬼神祭祀、民俗信仰、神話傳說和各種方技術(shù)數(shù)。由于道教具有所謂驅(qū)邪避禍、祈雨求晴、勸善懲惡、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乃至治國平天下等實用性很強的功用,古代中國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的社會各階層都普遍地對它感興趣,奉道君王代不乏人,雍正便是一個典型的崇道皇帝 。

雍正皇帝
雍正在皇子時代就直接或間接地與道士有交住,突出的一件事是他相信武夷山道士給他算的命 。
那時,諸皇子明爭暗斗,紛紛圖謀儲位。雍親王胤禛堅信天命,在政治廝殺中總想預(yù)知自己的前程 。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 胤禛的家人戴鐸前往福建任知府 ,
在給主子的一封信中寫道:武夷山有一道人,“行蹤甚怪,與之談?wù)?/span>,語言甚奇,矣奴才另行細細啟知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span>
胤禛見信,非常感興趣,立即批復(fù):“所遇道人所說之話,你可細細寫來?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span>就此,戴鐸回啟察道:“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將主子問他,以卜主子,他說乃是一個萬字。道人所算“萬”字命,讓雍親王胤禛振奮不已,由此也就對道士多有好感了。
在雍正的《藩邸集》中,有關(guān)道士、道教方面的詩文有不少,其中《贈羽士》2首,《群仙冊》18首,記錄了他在皇子時代與道士交往和對道教的向往等情況。雍正登基后,以帝王之尊倡導(dǎo)奉道。雍正五年(1727年),第5代正一天師張錫麟應(yīng)召入京,雍正沿襲明朝舊例,授予光祿大夫品級。同年,北京白云觀道士羅清山死去,雍正派內(nèi)務(wù)府官員前往料理喪事,并特地指示按著道家禮節(jié)從優(yōu)辦理,追封羅清山為“真人”。雍正九年,諭令撥庫銀l萬余兩,大修龍虎山上清宮,歷時兩年完工,又為龍虎山諸宮觀置買香火田340畝,還賜給御制碑文。雍正十一年下發(fā)專門諭旨,責(zé)令地方文武大員“加意護持出家修行人”。在清朝十帝中雍正保護道教算是最積極的了。
在今天保留下來的清宮檔案中,也有反映雍正參與道教活動的痕跡。僅是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的《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就有不少雍正傳旨設(shè)置斗壇、神牌、符咒、諭令制作法衣、
道冠等情況的記載,時間主要集中在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之間。這里有代表性地介紹幾例:其一,雍正八年十月十五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奉旨:“養(yǎng)心殿西暖閣著做斗壇一座?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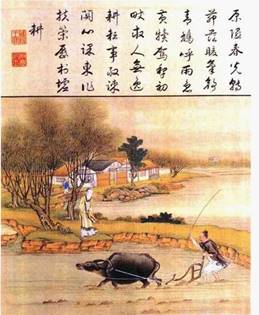
其二,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奉上諭:“朕看后花園千秋亭若設(shè)斗壇不甚相宜,用后層方亭設(shè)斗壇好?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其三,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根據(jù)雍正旨意,“頭等侍衛(wèi)兼郎中保德帶領(lǐng)催總劉三久、張四,序班沈祥,將舊做下黃銅符板一分安在養(yǎng)心殿訖;將木符板二分,太和殿安一分,乾清宮安一分?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span>
在雍正的親自安排下,紫禁城內(nèi)的養(yǎng)心殿、太和殿、
乾清宮這幾個主要宮殿都安置了五方符板,處在道神的保護之下。
其四,雍正卜年十月二十三日,司庫常保等進呈刻絲法衣一件,紅緞道衣一件。
雍正傳旨:“交蘇州織造處,照樣做刻絲法衣十件,紅緞道衣五卜件。”
僅是這一次,雍正就命蘇州織造做法衣、
道衣60件,可知在雍正操辦下法事之盛。
其五,雍正一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收拾得果托八十六件,供花大小四百六十六枝,木墩一個,五色符績五塊,五色牌位績七分,傘二把;并做得果罩九十件,爐蓋二仁二個,鐵八掛爐座,鉛條五根,神牌架三件,交首領(lǐng)太監(jiān)馬溫良持去。其圍屏隔斷墻三面內(nèi)安水陸欄桿,司庫常保帶領(lǐng)柏唐阿富拉他持進養(yǎng)心殿抱廈內(nèi)安裝訖?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span>這是一整套羽壇供器。雍正在正月忙著將其安設(shè)在寢宮養(yǎng)心殿的抱廈內(nèi),又從一個側(cè)面表明了他對仙道的崇好。
這里列舉的幾則檔案,并不足以反映雍正參與道教活動的全貌,但卻使我們看到,他對斗壇的形制、安置的地點,對符板的樣式、安設(shè)的方位,以及各類供器的制做,都是親自過問指點,表明他是實實在在奉道的。
那么,雍正為何如此竭力崇道呢?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道家所用經(jīng)典符章,能祈晴禱雨,治病驅(qū)邪,保國安民,其濟人利物之功驗,人所共知。
”原來雍正好道,意在求得道神的保護,驅(qū)邪祟避災(zāi)禍,以“濟人利物”。
雍正在尊崇道教的同時,力主“三教合公”、“
三教同源”。他認為儒、
佛、
道三教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教化臣民如何做人:“三教之覺民于海內(nèi)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span>
他還進一步闡發(fā)說:“道家之煉氣凝神”與“釋氏之明心見性”、“
吾儒存心養(yǎng)氣之旨”絲毫“不悖”,并且三教“皆主于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亦有補于治化。”
,在這里,雍正強調(diào),儒、
佛、
道三教在心性煉養(yǎng)上是一致的,其勸善戒惡利于王道的治化作用也是一樣的 。
歷史上,佛、道二教從來是矛盾重重互不相容的,歷代帝王不是崇道抑佛,就是尊佛壓道,著名的“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 、
北周武帝、唐武宗 、
后周世宗)毀佛事件即是明證。
雍正既然三教同奉,便以帝王之力在佛道之間大搞調(diào)和,他說“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強把佛道捏合在一起。
他收佛門弟子,卻接受了妙應(yīng)真人婁近垣;雍正編選佛家語錄,竟把道家紫陽真人張伯端的著述選了進去;他給沙門賜封號,沒有忘記道家張伯端,亦加救封;他認為張伯端的《悟真篇》,盡管是道家的著作,可在佛學(xué)中也是最上乘的。
雍正融儒、佛、
道三教于一爐,是他統(tǒng)治思想的高明之處。
他明確提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這確是一個封建君主對三教的絕妙利用。
-
以治病修身為旨趣的術(shù)士尋訪
道教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其著眼點在于現(xiàn)世利益,即重人生,樂人世,旨在追求長生久視,今生成道。
這與三大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 、
伊斯蘭教)僅僅企求靈魂的解脫,寄希望于死后(或者下輩子)的天國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道教強調(diào)修煉養(yǎng)身以永享超人間的快樂,修煉就要有相應(yīng)的方術(shù),所以道教特別重視方術(shù),以致道與術(shù)密不可分 。
道書(仙傳拾遺)就此談到:“術(shù)之與道,相須而行。道非術(shù)無以自致,術(shù)非道無以延長 ?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span>
道術(shù)被道家看作長生求仙的必要手段,由此各種各樣的養(yǎng)生術(shù)盡入道教天地,各類巫師 、
丹家、方士也都歸入到道教的名下 。
于是,自古以來追求煉養(yǎng)修身希望長生成仙的帝王,無不遍訪道家術(shù)士 。
雍正晚年多病,為療疾健體,他尋訪道家“異人”的活動幾乎沒有停止過 。

從現(xiàn)存清宮檔案看,雍正皇帝訪求術(shù)士是從雍正七年開始的 。
這年有兩次記載,一次是雍正七年二月十六日,雍正用朱筆在陜西總督岳鐘琪密折上批示,令秘密查詢終南山修行之士鹿皮仙,又名狗皮仙。岳鐘琪奏復(fù)說:此人實系瘋癡,一無道行可言 。
雍正帝就此作罷 。
另一次,在《起居注冊》、
《實錄》等官書中都提到過:雍正七年,怡親王允祥訪得白云觀道士賈士芳“精通醫(yī)術(shù)”,遂推薦給皇兄。可是,雍正召見后,感到這個賈道士對心性之學(xué)并無所知,沒有留用,略加賞賜就打發(fā)出去了。賈士芳于是浪跡河南一帶。
雍正八年春夏之際,雍正鬧了一場大病。為治病保命,康復(fù)長壽,雍正大規(guī)模地征訪名醫(yī)和精于修煉之士。其中,他命四川巡撫憲德訪求龔倫其人一事,很有代表性。這年二月二十八日,憲德奉到從北京發(fā)回的一件朱批奏折,里面夾有附片兩件,一件是雍正的御筆:“諭巡撫憲德:聞有此龔倫者,可訪問之。得此人時,著實優(yōu)禮榮待,作速以安車送至京中,…不必聲張招搖令多人知之?div id="4qifd00" class="flower right">
。”
憲德奉到諭令,立即派人查詢,于三月二十四日具折奏報:龔倫生于崇禎戊寅年,于雍正六年十二月無疾而逝,有子4人,長者65歲,幼者僅4歲 。
崇禎戊寅年是1638年,雍正六年系1728年,如此看來,龔倫“年90歲”之說不誤;幼子時年4歲,則是生于1726年,和“86歲猶有妾生子”之說也相近 。
龔倫其人善養(yǎng)生有異術(shù)則是可信的 。
可惜的是,龔倫已經(jīng)身故。雍正帝在嘆惜之余,在憲德的密折上批道;“其子中或有曾領(lǐng)伊父之道理者否?必須優(yōu)待,婉轉(zhuǎn)開示,方能得其實?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雍正訪求仙人的心情十分迫切,在命憲德尋找龔倫的同時,他給河?xùn)|總督田文鏡、浙江總督李衛(wèi)、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署川陜總督查郎阿、山西巡撫石麟、福建巡撫趙國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級官員,分別發(fā)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諭。內(nèi)容如下:
“可留心訪問,有內(nèi)外科好醫(yī)生與深達修養(yǎng)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倆遇緣訪得時,必委曲開導(dǎo),令其樂從方好,不可迫之以勢,厚贈以安其家,一面奏聞,一面著人優(yōu)待送至京城,脫有用處。揭力代朕訪求之,不必預(yù)存疑難之懷,便薦送朕人, 朕亦不怪也, 朕自有試用之道。
如有聞他省之人,可速將性名來歷密奏以聞,膚再傳諭該督撫訪查,不可視為具文從事,可留神博問廣訪,以符朕意。
慎密為之!”
這道朱諭,完好地保存下來,其中藏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9份,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大約6份。
通常,分別頒給各處官員的卜諭,如內(nèi)容文字相同,都假手于書吏,唯獨此諭,都是雍正用朱筆親自一份一份地書寫,一卜分工整,足見他對此事的慎密和重視。皇帝既然要臣下“留神博問廣訪”,“不可視為具文”,接件人怎敢怠慢,即刻展開行動,其中寵臣李衛(wèi)反應(yīng)最快,奉諭后的第二天,他便密折奏復(fù),說民間傳聞在河南的道士賈士芳有神仙之稱,特推薦該人進京為皇上治病。
雍正接到此奏,或許感到上年沒有留用賈士芳是失策了,他立即傳諭河?xùn)|總督田文鏡,速將賈士芳送京。賈于雍正八年七月間抵達宮禁,開始給皇上治病,竟頗見療效。對此,雍正十分高興,對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說:“聯(lián)躬違和,適得異人賈士芳調(diào)治有效?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可是,伴君如伴虎。就在這年九月間,雍正突然將賈士芳下獄治死。關(guān)于賈士芳的獲罪,歷來說法不一,現(xiàn)在,原始的宮中檔案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新證。在清宮檔案中,有一件經(jīng)雍正親筆修改的上諭,據(jù)推斷是雍正八年九月間所發(fā).在這道諭旨中,雍正說:賈士芳的“按摩之術(shù)”、“密咒之法”確是“見效奏功”,可是“一月以來,聯(lián)躬雖已大愈,然起居寢食之間,伊(指賈士芳)欲令安則安,伊欲令不安則果覺不適。”“
其調(diào)治聯(lián)躬也,安與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圍者。”雍正帝進而斥責(zé)賈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謂可施于聯(lián)前?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span>讀了這段諭旨,我們自然了解到賈士芳獲罪的真相,原來他利用道家的“按摩”、“密咒”方術(shù),逐漸控制了雍正的健康,而雍正一旦察覺到自己的身體安康要被賈道士操縱,頓感間題嚴重,遂刻不容緩地處理此事。

案發(fā)后,雍正一方面極力為李衛(wèi)開脫,說李衛(wèi)推薦時已聲明不知賈某底細,只是將所見所聞具奏,盡無隱之忠誠,只可嘉獎而無過錯:另一方面,諭令從速審處賈士芳。
朝中大臣秉承旨意,僅幾天時間便拿出處置意見,說賈某應(yīng)照大清律凌遲處死,其親屬則當處斬或沒為奴。
雍正為表示寬仁,命將賈士芳處斬,親屬各減輕了事。
賈士芳以“妖妄之技”被斬,雍正并沒有由此不信任道家,更沒有從此將道士杜絕于門外。
相反,雍正要找個更為高明的道士來做他的“醫(yī)療顧問”,這個人便是龍虎山高道婁近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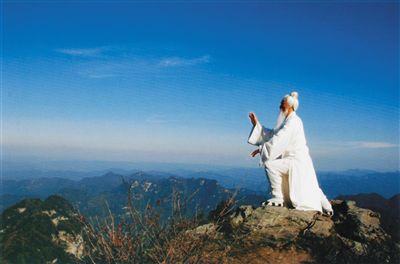
婁近垣是江西人,年輕時登龍虎山為道。雍正四年應(yīng)召入值京師。
他的得寵,是以賈士芳的喪命為開端的。
雍正八年九月,賈士芳被處斬后,雍正疾患未安,以為是賈士芳的“余邪纏繞”,便召婁近垣入內(nèi),設(shè)壇禮斗,以符水治療,不久果然病愈。
雍正身上的邪祟被治退,高道婁近垣遂備受恩寵,不僅賜給四品龍虎山提點、
司欽安殿主持,還被封為除妖的“妙應(yīng)真人”,并有旨特制法衣賞賜,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專為婁近垣承做繡黃緞法衣、繡黃紗邊綠紗心法衣、繡紅緞九龍法衣各一件。而且,前面提到的雍正在大內(nèi)御花園玉翠亭以東建造專門房舍“給法官住”,據(jù)考證這“法官”就是婁近垣,也應(yīng)當是說,道士婁近垣住進了紫禁城內(nèi)的御花園。
雍正身邊幾位有名的道家術(shù)士,婁近垣大概是唯一善終的。
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婁近垣很會揣摩雍正心思。雍正主張三教同源,婁近垣便以理學(xué)中“萬物皆備于我”和禪宗“即心是佛”的思想,來解釋道教中的“道”,“無心于道,故處處是道體”,這樣就和雍正三教一體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二是婁近垣雖以符篆道術(shù)致貴,但他很明智,從不炫言道教法術(shù)煉養(yǎng)之事。
史載:婁近垣“雖嗣道教,頗不喜言煉氣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謀生理耳。豈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也?”婁近垣作為得寵高道,在宮中一直呆到乾隆年間。
總起來看,雍正在宮中供養(yǎng)的道家術(shù)士,均屬“修煉養(yǎng)生之人”。
雖然其手段形式多樣,但目的都是為雍正治病養(yǎng)身。這當中有行念咒按摩術(shù)的賈士芳,有設(shè)壇禱祈驅(qū)祟的婁近垣,還有下面將談到的“為煉火之說”的張?zhí)?/span>、
王定乾。
-
以丹毒暴亡為終結(jié)的爐火燒煉
煉丹是道教達至長生久視的基本修煉方術(shù),歷史上煉丹家往往就是道家,故此人們也把道教稱作丹道。所謂丹,有內(nèi)外之分。
外丹,是指以天然礦物石藥為原料,用爐鼎燒煉,以制出服后不死的丹藥。
歷史上,有主張煉制和服餌黃金、丹砂的金砂派;有提倡以鉛汞為至寶大藥的鉛汞派;還有極言用硫磺和水銀合煉以求神丹的硫汞派。
內(nèi)丹,是通過內(nèi)煉使精、氣、
神在體內(nèi)聚凝不散而成丹,達到養(yǎng)生延年的修煉目的。歷代追求長生不老的帝王大多迷戀神丹大藥,刻意追求外煉的仙丹 。
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熱心燒煉服丹致死的皇帝 。
雍正在藩邸時期,就已對道家的藥石產(chǎn)生了興趣。他在那時曾寫過一首(燒丹》詩:
鉛砂和藥物,松柏繞云壇 。
爐運陰陽火,功兼內(nèi)外丹。
光芒沖斗難,靈異衛(wèi)龍皓 。
自覺仙胎熟,天符降紫鴦 。
這首詩宛如一幅煉丹寫真圖,從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對“內(nèi)外丹”有所認識了。
雍正即位后,極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師張伯端,封其為“大慈園通禪仙紫陽真人”,并軟命在張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觀以崇祀 。
據(jù)《紫陽道院碑文》載,雍正特別贊賞真人張伯端“發(fā)明金丹之要”。
至遲從雍正四年開始,雍正就經(jīng)常服食道士煉制的一種丹藥“既濟丹”。他自我感覺服后有效,遂將丹藥賜給寵臣服用。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鄂爾泰具呈奏折說,一個月前皇上賞賜的既濟丹服后“大有功效”,并言:“舊服藥方,有人參鹿茸,無金魷縹,今仍以參湯送之,亦與方藥無礙?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span>
雍正折尾批道:“此方實佳,若于此藥相對,聯(lián)又添一重寬念矣。
仍于秋石兼用作引不尤當乎?”。他是將傳統(tǒng)中醫(yī)醫(yī)藥與道家丹藥兼用并收了。
雍正還常把既濟丹賞賜給河?xùn)|總督田文鏡、
川陜總督岳鐘琪、
河道總督裕曾藥等其他封疆大臣。在賞給田文鏡丹藥時,雍正說他自己一直服用,沒有間斷過。他還對田文鏡說,這種丹藥“性不涉寒熱溫涼,征其效不在攻擊疾病,惟補益元氣是乃專功。”。這就十分清楚,雍正經(jīng)常服用這種丹藥,并不是為了治療某種疾病,而是專門用作彌補元氣,延年益壽。一般說來,人們服食丹藥,總不免有所顧忌,怕與身體不投,出現(xiàn)意外,為此,雍正勸田文鏡盡管放心,說:“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異,放膽服之,莫稍懷疑,乃有益無損良藥也。聯(lián)知之最確 。”
。
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藥的藥性,并且對他所服用的丹藥已是確信不疑了。
雍正不僅服食道士進獻的丹藥,還在圓明園升火煉丹 。
這本是機密事件,正史不見記載。可是,在清宮秘檔中仍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活計檔》中的一些原始記錄,就披露了雍正煉丹的一些情況 。
在這一檔冊中最早出現(xiàn)的有關(guān)記載,是在雍正八年十一 、
十二月間,共有4條:“十一月十七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 、
太醫(yī)院院使劉勝芳同傳:圃明園秀清村處用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四百斤。記此 。
(入匣作)”“十二月初七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 、
太醫(yī)院院使劉勝芳傳:圓明園秀清村處用鐵火盆革,口徑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紅爐炭二百斤。記此 。
(入匣作)”“十二月十五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太醫(yī)院院使劉勝芳 、
四執(zhí)事執(zhí)事侍李進忠同傳:圓明園秀清村處用礦銀十兩,.里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記此。(入匣作)”“十二月二十二日,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四執(zhí)事執(zhí)事侍李進忠傳:圓明園秀清村處化銀用白炭一千斤,渣煤一千斤 。
記此。(入匣作)”
在此就這四則檔案作幾點分析。第一,匣作何以需用如此之多的燃料?幾條檔案都注明物品傳用歸入匣作,這個機構(gòu)專門承做各類器皿文具需用的木匣或紙板匣,匣子表面多用續(xù)錦糊飾。因此配給匣作的燃料無非用于粘匣所需膠料漿糊的熬制。可是,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內(nèi),竟耗用桑柴、煤炭440斤,顯然其用途不限于制匣。這里要說明的是,清代宮苑取暖備膳所用煤柴向有定例,并設(shè)專門檔冊記載,是從不載入《活計檔)的。
第二,傳用物品的地點秀清村,位于圓明園東南隅,背山面水,于一分僻靜,是個進行秘事活動的好去處。
第三,傳用物品的官員,除了雍正相當信任的心腹內(nèi)務(wù)府總管海望外,還有主管帝后醫(yī)療保健的太醫(yī)院院使劉勝芳,這點足應(yīng)引起關(guān)注。
第四,更重要的是,傳用物品中既有大量燃料,又有“礦銀一兩”,還有“化銀”之說,據(jù)此可以推斷,雍正八年末,在圓明園秀清村開始為雍正治病療疾燒煉丹藥。雍正丹爐一開,燒煉之火便沒有熄滅。在雍正九年到十三年的(活計檔)中,這類記載便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了。如雍正九年的“六所檔”.雍正十年的“南薰殿并圓明園頭所、四所、六所、接秀山房總檔”,雍正十一年的“四所等處檔”,雍正十二、十二年的“六所檔”,都有這類內(nèi)容。根據(jù)造辦處這些檔案記載,雍正為燒煉丹藥,在這一時期傳旨進用的煤192噸,炭42噸,此外還有大量的鐵 、
銅 、
鉛制器皿,和礦銀 、
紅銅、黑鉛、硫磺等礦產(chǎn)品,以及杉木架黃紙牌位、糊黃絹木盤、黃布(絹)桌圍、黃布(絹)空單等。這些物品,都是煉丹活動所必不可少的。據(jù)統(tǒng)計,自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的59個月份內(nèi),共傳用煉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月兩次半還多。傳用物品的地點基本都在圓明園內(nèi)。由此可以想見,在雍正的旨意下,成百噸的煤碳被運進皇家宮苑,在長達幾年的時間里爐火不滅,煉丹不止,把個山清水秀的圓明園變成道家洞天福地!
據(jù)史料記載,為雍正練丹的道士主要有張?zhí)?/span>、王定乾等人。他們深諳“修煉養(yǎng)生”,“為煉火之說”,在圓明園主持爐火燒煉事宜。張?zhí)?/span>、王定乾等沒有辜負雍正的期望,煉出了一爐又一爐的金丹大藥。雍正服后,感覺良好,便拿出一些作為賜用物品,像原來賞既濟丹一樣,賞賜給出征將士。(活計檔》載,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間,雍正帝曾兩次賞發(fā)“丹藥”。
一則:“三月二十一日,據(jù)圓明園來帖內(nèi)稱,內(nèi)大臣海望交丹藥四匣,傳旨:配匣發(fā)報,賞哥理大將軍查郎阿、副將張廣油、參贊穆登、提呀類廷。欽此。于本月二十五日,將丹藥四匣配得杉木箱一件,風(fēng)毯包裹,稀花塞墊,領(lǐng)催趙牙圖交柏唐阿巴蘭太持去訖。”
二則:“四月初一日,圓明園來帖內(nèi)稱,委哥主事寶善來說,內(nèi)大臣海望文丹藥一匣,傳旨:配匣發(fā)報,賞散狄大臣達奈。
欽此。于本月初四日,做得杉木匣一件,外包黑毯,交柏唐阿巴蘭太去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