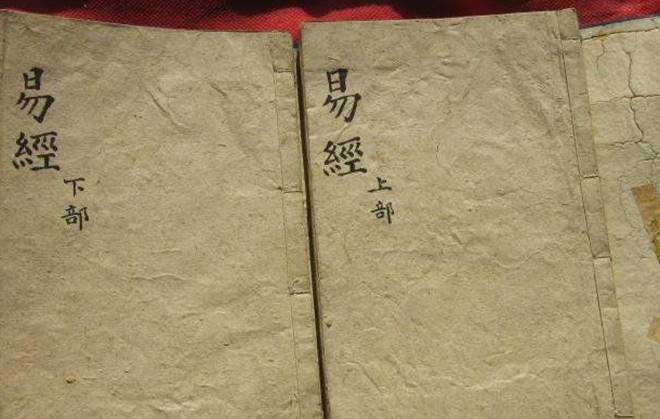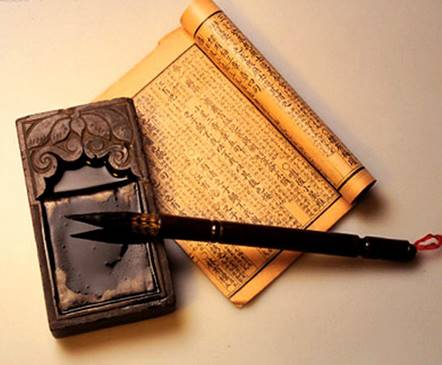章偉文
內(nèi)容提要:本文認(rèn)為 ,道教易學(xué)是以《周易》卦爻象、卦數(shù)及歷代易學(xué)中圍繞著《周易》經(jīng)
、傳及其闡釋而出現(xiàn)的概念
、命題等來對道教的信仰、教義思想進(jìn)行解說的一種學(xué)術(shù)形式
。道教易學(xué)主要為解決不同時期之道教教義
、信仰中的人天關(guān)系問題而提出,并形成了具有不同時代特色的道教易學(xué)形式
,如宋元明清時期的易學(xué)
內(nèi)丹學(xué)、道教易圖學(xué)和道教易老學(xué)等。開展道教易學(xué)的研究
,對于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界探討價值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關(guān)系
、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以及理想人格塑造、現(xiàn)代文化精神塑造等問題有啟示意義
。
關(guān)鍵詞:道教易學(xué)分期與特征意義
《道藏》中基本沒有完整的、專門通過對《周易》經(jīng)、傳的直接注解來闡發(fā)道教信仰
、教義思想的經(jīng)文
。
①盡管如此,道經(jīng)中運用《周易》之理及其卦爻象來闡發(fā)道教的信仰和教義思想的情況卻不在少數(shù),并因此而形成了道教義理學(xué)的重要一枝——道教易學(xué)。所謂道教易學(xué),主要指的是道教中的易學(xué),即以《周易》的卦爻象、卦數(shù)及歷代易學(xué)中圍繞著《周易》經(jīng)、傳本身及對其闡釋中出現(xiàn)的種種概念、命題來對道教的信仰尤其是教義思想進(jìn)行解說的一種學(xué)術(shù)形式 。
一 、
道教易學(xué)確立的理與勢
道教易學(xué)是否僅是一種純主觀的設(shè)定?其產(chǎn)生的思想淵源和歷史背景如何 ?為什么能從道教中發(fā)展出道教易學(xué)的思想體系
?等等這些問題,決定了我們必須考察一下道教易學(xué)確立的理
、勢問題
。
道教易學(xué)的出現(xiàn),是與整個漢代社會的政治 、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密不可分的
。因為中央集權(quán)政治統(tǒng)治的需要,漢武帝實行
“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shù)
”的方針 ,使儒家學(xué)說成了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作為意識形態(tài)
,要對現(xiàn)實生活進(jìn)行引導(dǎo)
、規(guī)范,要對至高無上的王權(quán)進(jìn)行監(jiān)控
,故而以孟喜
、京房為代表的漢儒官方易學(xué)的主要特點在于通過卦氣說、奇偶之?dāng)?shù)
、納甲之法等解《易》形式
,言陰陽災(zāi)異來探尋
‘4天意”,利用“天意”來對現(xiàn)實的王權(quán) 、人事進(jìn)行規(guī)范
。到東漢中后期又出現(xiàn)了講陰陽變易和爐火修煉之事的最初的道教易學(xué)。這是因為
,儒學(xué)的獨尊對于漢代社會有利有弊
。其利在于儒家的綱常倫理及其重教化的傳統(tǒng)能發(fā)揮穩(wěn)定社會
,鞏固皇權(quán)的作用
;其弊則反映在儒家的一套定型的綱常倫理與活生生的、不斷發(fā)展的社會生活之曬常存在一種“發(fā)展,,和“限制,’的矛盾,在一定情況下,可能會激化為主要矛盾,導(dǎo)致社會變革。
《道藏》收有明李贊《易因》,但此書的目的并不在于闡發(fā)道教的信仰教義,它具有更多、更濃厚的儒學(xué)色彩。相對于漢代儒學(xué)的僵化,先秦道家思想則顯得通融、無礙。先秦道家“道”的概念具有無限的包容性,一切變與不變皆可納人其中。但是道家具有輕人事、重天道的特征®,這使其在切人現(xiàn)實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難度。而不能切入現(xiàn)實,則不能引領(lǐng)現(xiàn)實。先秦道家的這個理論缺陷,使它必須適應(yīng)新形勢而作出某種改革,而道教便是先秦道家變革后的一個產(chǎn)物。道教以“道”名教,直接繼承了先秦道家通融無礙的“道”的思想 。但道教作為一種宗教
,亦應(yīng)考慮教化世人的問題,因此也就要考慮如何更好地教化現(xiàn)實
、切人現(xiàn)實的問題
。道教既吸收了先秦
k家在人天關(guān)系上的思想,又吸收了儒家重人事、重現(xiàn)實教化的特點,對天人關(guān)系進(jìn)行了重新審視。它一方面認(rèn)為人道應(yīng)該合于天道,天道是人道歸趨的目標(biāo);另一方面又重人道之本身,認(rèn)為歸趨于天道的落腳點還在于人道。我們無論從太平道的“大方”、“小方”,還是早期天師道的“二十四治”、“二十八治”、“靖廬”、“廚會”、“祭酒”、“鬼卒”等一系列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形式,都能看出道教的上述特點。
天道之理為何?理想之人道為何?由人道及于天道為什么是可能的?由人道及于天道的具體路徑為何?道教正是在對這些人天關(guān)系問題的思考過程中,引人了《易》學(xué),從而確立了道教易學(xué)這種獨特的道教教義理論形式。因為《周易》經(jīng)、傳的義理內(nèi)容和卦交象的數(shù)理排列,如卦氣說、納甲說、卦的數(shù)理、卦序的排列、卦的取象、陰陽對待流行的觀念、陰陽與五行、八卦的關(guān)系等,對于天道的敷演,在當(dāng)時是非常有效的理論形式。將《易》引人道教,可以解決由人道及于天道的路徑和階次的問題。人通過法陰陽的消長,如四時、十二月
、二十四節(jié)氣的卦氣變化,卦象和卦理的變化
,納甲的方法
,修丹以合于天道。由人道及于天道的路徑和階次等問題因《易》被引人道教而變得更加明晰
。
因道教與《易》的溝通,產(chǎn)生了道教易學(xué),也便形成了道教易學(xué)獨特的論題
:首先:道教易學(xué)結(jié)合《易》之理,要探討天道及其表現(xiàn)
,以為道教信仰確立終極的宗教目標(biāo),也為道教的宗教修持確立方向
。因此
,以《易》的理
、象
、數(shù)等形式來論何謂道
,道與物的關(guān)系,道的各種屬性
,道的特征等
,均屬道教易學(xué)的內(nèi)容。其次
,道教易學(xué)結(jié)合《易》之理
,要探討修道的路徑和方法,使道教的宗教修持切實可行
。因此
,以《易》的理、象
、數(shù)等形式來論修道的方式
,如藥物問題、火候問題
、鼎器問題
、路徑問題、層次問題等
,也都屬道教易學(xué)的內(nèi)容
。第三、道教以及道教易學(xué)都是要立足于人事教化
,以人合天
,從而得道成神、成仙
,長生不老
。因此,道教易學(xué)的內(nèi)容還應(yīng)包括以《易》的理
、象
、數(shù)等形式來論人性的修養(yǎng)和人的精神超越,對于生與死問題的思考
,對于終極價值問題的思考
,以及對社會現(xiàn)實所應(yīng)采取的合適的態(tài)度等問題。

二、道教易學(xué)的歷史分期及基本特征
(一)早期道教與易學(xué)的關(guān)涉
早期道教,一般認(rèn)為,以太平道
、天師道和金
丹道為代表
。太平道的主要經(jīng)典是《太平經(jīng)》,天師道的早期經(jīng)典是《
老子想爾注》
,而金丹道教則以《周易參同契》作為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
這三種早期的道教著作都與《周易》有較密切的關(guān)系。之所以如此,亦與當(dāng)時的社會環(huán)境有較一定的關(guān)系
。東漢后期
,外戚和宦官輪流掌權(quán),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民不聊生
,國家處在危機四伏的動蕩之中。如何引領(lǐng)社會走上正軌
,或者說
,怎樣將現(xiàn)實社會的種種黑暗消除,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社會
,是時代提出的一個大問題
。太平道以一種宗教信仰的形式來解決這個時代課題。它認(rèn)為現(xiàn)實世界是不合理的
,是注定要滅亡的
,所謂
“蒼天當(dāng)死,黃天當(dāng)立,”黃天即
“太平世界”。
“太平世界”之所以能取代現(xiàn)實世界,主要就在于現(xiàn)實世界的不合理和“太平世界”的合理。而
“太平世界”的合理,除了它具有宗教理想的性質(zhì)之外,亦有其理論的基礎(chǔ)
。這個基礎(chǔ)就在于
,
“太平世界”是合于天地之道的、是順應(yīng)天地陰陽五行之則的。而在漢易中
,陰陽五行思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故在太平道的重要經(jīng)典《太平經(jīng)》中
,亦對漢易的思想加以吸取融會
,以構(gòu)成其道教教義的思想體系。

《太平經(jīng)》重視人與天地陰陽的相合;在對陰陽關(guān)系的考察過程中,重視陰陽本身的相和
;認(rèn)為陰陽的變化,有其內(nèi)在的規(guī)律。陰陽或消或長
,表現(xiàn)出刑與德兩種不同的屬性
。《太平經(jīng)》以漢易的十二辟卦來論陰陽的刑德與消長
,目的在于使人君能深知天地表里陰陽之氣的消長
,從而興陽氣
,抑陰氣,重德而不重刑
,達(dá)到垂拱而治
,無復(fù)有憂的境地
。這是對漢易卦氣說內(nèi)容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
。《太平經(jīng)》還對《周易
?說卦沖八卦方位說的難通之處作了創(chuàng)造性地說明,①以天地間陰陽消長
“陽極陰生,陰極陽生
”等規(guī)律性認(rèn)識對之作出解釋?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短浇?jīng)》引《易》人道 ,目的在于論證道教的教義和信仰。這是在東漢后期社會矛盾日益加深
,人們力圖尋求在現(xiàn)實中創(chuàng)建一個理想社會的強烈愿望以一種宗教信仰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結(jié)果
。而早期天師道也和太平道一樣,將宗教理想與社會理想相結(jié)合
,希望按宗教的理想來引領(lǐng)
、改造不合理的現(xiàn)實社會。它認(rèn)為人人
“謙信” ,就能消除戰(zhàn)亂
,在人間建成理想的社會。如其早期重要經(jīng)典《老子想爾注》吸收《周易》《謙》卦的思想
,以之解《
道德經(jīng)》
,提出
“道意謙信”的觀點。②
但是 ,《太平經(jīng)》和《老子想爾注》對《易》理的運用
,基本上還是處于局部的、零星的
、不系統(tǒng)的狀態(tài)
,而真正系統(tǒng)地運用漢易思想論述道教的信仰和教義,建立起真正意義的道教易學(xué)
,還應(yīng)首推《周易參同契》
。《周易參同契》推闡《易》之天道
,以之來引領(lǐng)人事
,又以人事去印證《易》所言之天道
。在這個過程中
,和太平道
、早期天師道有所不同
,金丹道主要以個體的人為本位,通過個體的人修金丹爐火之事
,使人道合于天道
。這是金丹道對于治理東漢亂世社會開出的一劑藥方。對于《周易參同契》的道教易學(xué)內(nèi)容和特征
,歷代學(xué)者都有評說
,其中又以南宋大儒朱熹論之尤精。他說
:“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棄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日用功之進(jìn)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而兩之。蓋內(nèi)以詳理月節(jié),而外以兼統(tǒng)歲功。其所取于《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認(rèn)為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系統(tǒng)地運用了《周易》的卦象和原理 ,以論天道和丹道爐火之理
。如《周易參同契》以
“乾、坤 、坎
、離四卦
”以為陰陽之橐籥;以乾 、坤
、坎、離之外的屯
、蒙六十卦論一月三十曰每日早晚之火候
;以坎 、離兩卦結(jié)合震、兌
、乾
、巽、艮
、坤六卦論月亮的盈虧
,說明一月中用火的程序;以復(fù)、臨
、泰
、大壯、夬
、乾
、娠、遁
、否
、觀、剝
、坤十二辟卦結(jié)合律呂以論一月或一年丹道爐火之用功
。因此
,我們可以認(rèn)為
,《周易參同契》已建立起較為系統(tǒng)、完整的道教易學(xué)思想體系
。
(二)魏晉南北朝道書中的易學(xué)內(nèi)容及其特征
東漢后期,《周易參同契》確立了道教的解易系統(tǒng)。但進(jìn)人魏晉南北朝之后,《周易參同契》的道教解易系統(tǒng)在道教內(nèi)外似乎都相對沉寂,沒有得到更進(jìn)一步地闡發(fā)。我們認(rèn)為,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受漢代黃老道勢衰的影響,®也與佛教傳入中國有關(guān)。
受佛教傳入的影響,進(jìn)入魏晉南北朝之后,理論界逐漸拋棄了對漢代天人感應(yīng)問題的討論,進(jìn)而將關(guān)注點轉(zhuǎn)向了探討現(xiàn)實之后的本體問題。這個學(xué)術(shù)的轉(zhuǎn)向,是導(dǎo)致《周易參同契》為代表的道教易學(xué)在教內(nèi)外沉寂的重要原因。因為從東漢中后期開始,一直到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總是處于動蕩和不穩(wěn)定中。要探究造成社會動蕩和不穩(wěn)定的原因,離不開對現(xiàn)實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檢討。制度的好與壞,當(dāng)然必須通過社會的實踐來評判,但對于一項制度形成的根據(jù)和原因的探討也很重要。一項好的制度,其形成的原因和機制是什么?一項不好的制度,為什么它是不好的?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必然引導(dǎo)人們?nèi)ヌ接懍F(xiàn)象和事物背后的決定性的因素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它是什么等問題。在這一點上,佛教認(rèn)為現(xiàn)實世界是虛幻不實的、本體的世界才是真實的,這一重視對現(xiàn)象背后的本體進(jìn)行思考的理論思路的價值就自然而然地流行起來。魏晉玄學(xué)吸收了佛教重本體思考的理論思路,適應(yīng)時代的需要,對有無本末的問題,對名教與自然的問題進(jìn)行了重點思考,這個思考主要是通過對《老》、《莊》、《易》三玄之學(xué)的闡發(fā)來進(jìn)行的。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之下,漢易的象數(shù)學(xué)似乎已經(jīng)被玄學(xué)易所超越。《周易參同契》主要就是結(jié)合漢易象數(shù)學(xué)來論道教的煉丹,因漢易象數(shù)學(xué)在魏晉時的命運,也直接影響到《周易參同契》在魏晉時期的發(fā)展。因玄學(xué)的話語系統(tǒng)成為當(dāng)時的主流文化,《周易參同契》不合時宜的漢易象數(shù)學(xué)話語系統(tǒng)不為時代所重,故不能不相對地沉寂。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易學(xué)仍然有所發(fā)展,其主要的特征是,魏晉南北朝的道教易學(xué)更為重視對《周易》神化和信仰化。主要表現(xiàn)在這一期的道書中,有較多關(guān)于八卦神、八卦壇場、道教八卦法器的記載。①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逐步走向成熟,從而要求宗教神系構(gòu)成
、宗教儀規(guī)的體系完善等方面的同步發(fā)展有關(guān)
。因為作為一種成熟的宗教,既要求其具備有核心的教義思想體系
,亦需一套完整
、成熟的宗教儀規(guī)及一定規(guī)模的宗教教團組織等因素與之相配。魏晉南北朝時期
,道教取得較大的發(fā)展
。故在其核心教義思想的指導(dǎo)下,構(gòu)筑一套完整的宗教儀規(guī)的問題便被提上了議事曰程
。道教通過對《周易》卦交符號進(jìn)行神化和人格化
,對之注人道教信仰的因素,達(dá)到了完善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儀軌制度的目的
。
(三)隋唐道教易學(xué)的復(fù)興
隋唐時期,道教得到了較快發(fā)展,《周易參同契》的影響也逐漸加大
。新
、舊《唐志》已有對《周易參同契》的記載
;在唐代,直接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周易參同契》的兩種外丹注本,即《道藏沖托名陰長生的注本和容字號無名氏的注本;在當(dāng)時的很多煉丹著作中,直接稱引《周易參同契》文句的情況較為普遍。為什么隋唐之后《周易參同契》的影響會逐漸增大?這一時期道教與易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如何?試作簡略分析。
從思想史和道教史的發(fā)展角度看,受佛教中觀“有無雙遣”思想、魏晉玄學(xué)思想的影響,六朝后期至隋唐時期,道教中有“重玄”學(xué)派的興起。所謂“重玄”學(xué)派的“重玄”,取自《老子》首章“玄之又玄”,并以之而開宗明義。重玄學(xué)比玄學(xué)更進(jìn)一步。玄學(xué)興起的原因在于探究現(xiàn)象背后的本體的需要,并在有與無的范疇之內(nèi)來討論此問題。重玄學(xué)超出了玄學(xué)的“有”與“無”,它雖然也是為了求證最終的本體
,但這個本體在確立的過程中,排斥任何規(guī)定性
,既不
“貴無”,亦不
“崇有”,也難說就是“獨化,,
。重玄學(xué)所設(shè)定的終極本體是一種
“玄之又玄”、“有無雙遣”、
“無滯無累”、
“超凡脫俗”的最高宗教精神境界。僅就學(xué)術(shù)思辨的水平言,相對于魏晉玄學(xué)
,重玄學(xué)有了長足的進(jìn)步。因為從思想本身的發(fā)展看
,從對宇宙生成本原的考察
,過渡到對現(xiàn)象背后的本體的考察,再到諸多對本體思考中的心性本體的凸顯
,這個過程涵蓋了對于世界的形成
、世界的本質(zhì),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等重要哲學(xué)命題的思考
,呈現(xiàn)出人類在哲學(xué)思考理路上的進(jìn)步和哲學(xué)內(nèi)容的豐富和發(fā)展
。同時,重玄學(xué)的目的主要在于引導(dǎo)人們?nèi)コ龑ΜF(xiàn)實的執(zhí)與滯
,排解種種矛盾
,直接契人本體。它直接開啟了道教義理學(xué)的心性之路
,這是道教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儒
、釋、道三教互融互攝的思想背景下
,尋求自身發(fā)展的一個新突破
,其功效性是不容抹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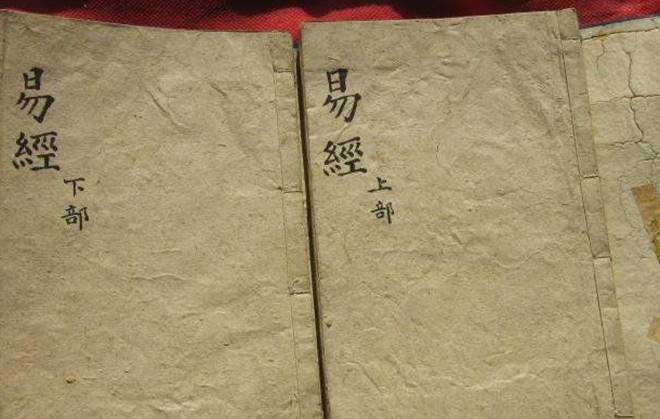
但重玄學(xué)用來論證本體的方式、方法主要是
“否定” 。隨著發(fā)展的深人,這種
“絕對否定”的方法論原則越來越構(gòu)成對道教傳統(tǒng)“重現(xiàn)實教化”宗風(fēng)的破壞 。而思想反作用于現(xiàn)實的功效性的大小
,畢竟是人們在進(jìn)行思考時必須要顧及的功利性原則。道教教義思想的建構(gòu)
,也是如此
。道教的現(xiàn)實教化不僅表現(xiàn)在要因應(yīng)、體察現(xiàn)實制度和生活以立教宗
,還表現(xiàn)在哲學(xué)思考上
,應(yīng)建立起現(xiàn)實與本體之間建設(shè)性地
、實在地聯(lián)系,而不能僅用絕對否定的方式來割裂現(xiàn)實與本體
,使現(xiàn)實與本體裂為兩截
。應(yīng)該說,道教重玄學(xué)在理論特色上更近于佛教中觀學(xué)的出世主義
,而與道教一貫重視現(xiàn)實教化的傳統(tǒng)有所悖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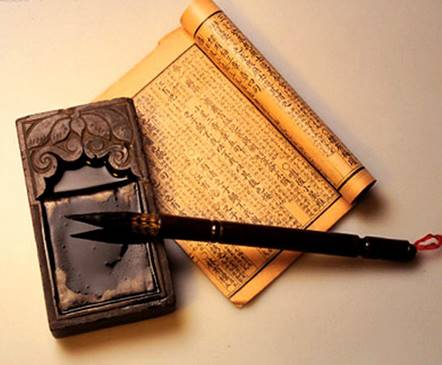
所以,隋唐道教義理學(xué)在建構(gòu)中,又重新關(guān)注《周易參同契》
,以肯定天道思想,重建人天關(guān)系的新理路
。隋唐以來
,道教各家在對《周易參同契》注釋的過程中,以漢易的卦氣說
、陰陽五行說
、納甲之說等等為基礎(chǔ),對宇宙的發(fā)生
、發(fā)展亦即天道進(jìn)行說明
。其共同點就是認(rèn)為天道不離陰陽消息,陰陽消息的規(guī)律可以《周易》卦爻變化的規(guī)律來表征;《周易》卦爻的變化反映的是天道的內(nèi)容